“五情”说之“尽而不汙”
第四情,“五情”里头第四情就是“尽而不汙”。就是把事实照实来说,尽其事实不加以汙曲。这汙,根据杜预(的解释)就是因为做假借字借为辶字旁的迂,或者是纟(通“糸”[mì])旁的纡,都是汙曲的意思。
但是日本学者竹添光鸿却有不同意见。他把这字,本来是污字,杜预把它读为假借字,所以才念作汙,它本来是污。所以竹添光鸿说不是假借字,根本就是“污”字,就是表示误会的意思,尽而不污,就是说尽其事实,就(是)误会的事情,也不加以隐瞒,把所有事情表明清楚,就把这污读为误会的误。
钱锺书先生又有另外一种意见,他认为这个字是假借作夸,是夸大的夸。他就说在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里头,“微”跟“显”、“志”跟“晦”、“婉”跟“成章”都是相反而相成。但是,杜预说读作“汙”,他认为不对,如果读作汙就是表示尽而直,因为杜预又说去直书其事,不加以委曲,那么就是又尽又直,就好像同一个意思,就是一再重复,那么就是骈枝叠架,他认为是太重复了,跟前面三句(的)句式、句法不相同。所以他认为如果是直,但是直不一定尽,就是可以直接地记载,但是不一定很详细,但是如果你去尽,你的事,所有的事情都说清楚了,没有不直的。所以他说根本不需要那么重复,他就引用了孟子、荀子还有庄子,最后认为这是“夸”的假借。就是庄子所谓“溢言”,就是超越了,就(是)说太多了,所以他认为尽而不夸,就是不加以隐讳,去如实、得当地记载,很周详,很详细,但是没有加饰,没有夸大,这就是尽而不夸,他读作尽而不夸,他用了一个英文,他说就是the whole truth,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
钱锺书这样说对不对呢?我觉得不太对。因为“微”跟“显”、“志”跟“晦”,“微”就是微隐,不清楚,跟明显,当然是相反。“志”就记载,“晦”就是不清楚,你把它加以记载,一般应该清楚,但是最后的效果是不清楚,那么也可以说是相反。但是“婉”跟“成章”就不是相反,“婉”是委婉,“成章”就是写成篇章,那么用委婉的方式写成篇章,就是用什么方式来写,所以就不是相反,“婉”跟“成章”不是相反,所以我们可以说“婉而成章”,也可以说“直而成章”,就是委婉地写或者是很率直地写,所以“婉”跟“成章”不是相反,“直”跟“成章”也不是相反。钱先生比较重视同一句里头字义的关系,但是忽略了上下句的关系。我们看“微而显”跟第二句“志而晦”,两句的句意是相反的。那么“婉而成章”跟“尽而不汙”,两句(的)句意也是相反的。所以杜预用“曲”来解释这个“汙”,就(是)汙曲,用“汙”。他认为,是纟(通“糸”[mì])字旁或者辶旁的汙的假借,就是“尽而不汙”主要是照顾句式,使它跟“婉而成章”句式差不多,我们说“尽而不汙”句意跟“婉而成章”,正好相反,所以(这个是)第一、第二句“微而显”“志而晦”是句意相反,然后第三句跟第四句,“婉而成章”“尽而不汙”也是句意相反,应该这样去看。那么竹添光鸿他把那字念为“污”,污秽的污,那个就(是)不对的。我们看“尽”跟“不汙”,虽然意思是相关,但是还不至于好像就(是)钱(先)生所说的“骈枝叠架”。钱先生认为这个字念作“夸”,是夸的假借,就说不隐、不讳,不加以隐讳,而如实得当,是很周详的,但是没有夸大。就是所谓尽而不夸,这是钱(先)生的说法,但是他所说的固然是史家的悬鹄,是这个很高的一个目标,但是就是历史(学)家的目标,《春秋》是经学,注重的是褒贬,不重在如实地记载。我们一定要明白,《春秋》是一个经,不是单纯的历史。
我举个例子,鲁隐公三年的《春秋》经,它说“三月庚戌,天王崩”。“三月庚戌”就是三月十二日,周平王驾崩。其实这个日期,三月十二日,不是真实的,真实的日期是三月二十四日,所以《左传》就说其实是“三月壬戌”,二十四日周平王驾崩,但是在讣文里头就写了,是庚戌那一天驾崩,提前了12天,在讣文里头提前了。为什么要提前?因为当时周天子的势力太弱了,诸侯都不重视他,周(朝)的大夫他就怕诸侯很晚才来吊祭周平王,所以就想诸侯早一些来,所以他这个讣文里头就把日期提前了12天,就让诸侯不会太晚才到。那么《春秋》所记载的不是正确的日期,但是为了表示作为臣下,这样地怠慢周天子是不对的,要表示诸侯不对,所以记载的时候就记载那假的、错误的日期。所以钱先生以一般史学观点,一般史学观要很准确,对不对?一定需要如实地记载,但是这个跟《春秋》是两码事,所以钱先生没有明白,没有了解,《春秋》是经,不是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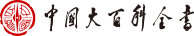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8139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813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