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天文学——追寻失落的文明(二)
可以看到陶寺的缝是非常细的,那么这样的话也就有助于我们实际上可以把这些节气精确地定在一定的位置。一开始以至于我第一次到陶寺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这些缝太细了,你看着会有点难受。但是到后来,你发现实际上是视觉面就这么大的时候,你就一点都不觉得奇怪了,因为它的缝隙,大概一厘米宽的这种缝隙和视觉面是非常相关的。这个是我们后来对它的一个大概的判断,就是在E13号缝这块正好是月北至,在E1号缝下面是月南至,中间的日南至,也就是说冬至、夏至以及春分、秋分都恰好能够跟缝隙相吻合上。这个是首先我们对陶寺观象台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它作为一个地平历系统就已经慢慢地被大家所熟知了。但是现在还有一些奇怪的就是其他那些缝隙的这些日期究竟代表什么,我们还不是太清楚,因为那时候的节气系统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后面又有一些新的线索,至少这些天文基本点已经可以给我们一些概念,它可能是一个地平历的历法系统。这是迎日祭祀,当然考古学家在周围也会发现到一些这种骨,所以就是说,古代的天文观测和这种祭祀活动是紧密相关的,它不是完全割裂的。
刚才讲的就是说当时发现了陶寺这个东西,应该说在考古天文学这块是一个很大的发现了。那么席泽宗院士在生前在讲到陶寺的时候,他也认为“陶寺观象台的发现应该是标志着中国考古天文学真正的诞生”。因为当我们有一些这样的遗址之后,我们就会吸引越来越多的类似这样的东西。大家可能会奇怪说为什么考古天文学这两年开始慢慢地多起来,原来没有。一个是我刚刚说的,过去几十年,我们做了大量的文献的工作,对实际关注并不多。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考古学实际上也是在最近几十年开始大发展,为什么大发展?因为我们城市建设太快了,今天修个路,明天挖个地铁,有大量的东西都被挖出来了,过去实际上这些东西是进展很慢的,所以这些年有大量的新的遗址被发现,有很多的遗址也等待我们去探索。
然后我就要讲到圭表测影,实际上最早的时候我在从硕士开始,我最早是做圭表测影的,本来并没有特别深入地来介入考古天文学,做圭表测影慢慢地就做到一起去了,最后会讲到一个殊途同归的问题。首先,圭表测影是什么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但是这么古老的方法我估计现在在天文系可能也不会有人再去做了。但是在古代,圭表测影(却)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天文技术,因为它是最简单的天文技术,只需要一根棍就可以观测。它也是延续时间最久的,几千年的过程里面都有圭表测影。我们之前最早发现的圭表是东汉的仪征铜圭表,已经做得非常漂亮了,它还可以翻,是一个折叠性的,就跟我们弹簧刀似的,做得很漂亮。明清的这种大圭表大家也很清楚。到元代的时候,郭守敬又做了四丈高表。
这个是在登封的测影台,有这样的一个石桩子,上面写着“周公测影台”五个字。1939年的时候,中央研究院的董作宾他们对这个地方进行了考察,也有一个考察报告专门出来。他们就认为这个桩子实际上是唐代人立的,并不是原来周公在这地方测的,但是也就是说唐代就传说周公曾经在这个地方测影,在我们很多古代的文献里都传说周公测影,而且周公测影还有不同的版本。比如说像《周髀》里面标出来的冬至影长一丈三尺五寸,夏至影长一尺六寸。就是《周礼》里面要稍微短一点,是一丈三尺和一尺五寸。它还有不同的数据,但是不管《周礼》还是《周髀》都宣称是周公做的。当然我们不知道它究竟是谁做的,在文献学上现在也有很大的争议,究竟是什么年代的我们不清楚。至少大家都传说周公曾经测过影,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同样,在明清的时候,就是铜制圭表,这个圭表现在很常见,在南京紫金山上就有。那是明代的一个铜圭表,在北京的古观象台也有。所以这样的圭表很常见了,在明清时候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建制,这个圭表它的高是八尺。实际上圭表在中国所有的文献里都是八尺,从来没变过。但是你测出来的影长也是尺寸,所以其实是一个比例关系,它究竟是多长我们也并不太关心,反正是八尺表,测出来影长是多少,它这个比例是对的。
但是根据我们最新的一些考证,就是中国古代的度量衡虽然经历了很多变化,但是它有一种度量衡叫天文尺。大约一天文尺是25厘米左右,实际上天文尺没有太大的变化。虽然市尺变化很大,但是天文尺始终是这么样一个规制。
在元代的时候,郭守敬就做了四丈的一个高表,他做这个东西是当时他在做《授时历》的改历,那么他为了获得更精确的一些数据,他认为把圭表能够变成原来的几倍之后,那么我的误差就会更精确。他同时还做了景符,那么通过这些观测就能够让圭表测影达到一个更精致的状态。从我们现在用天文学理论都可以很简单地对他当时的数据进行验证,实际也证明郭守敬的观测确实是非常准的。郭守敬所记载的这些天文数据,基本上它误差在元代以后也没有多大了,非常小了。郭守敬之前的就是从唐代到元代之间的误差还稍微要略大一点,那么也反映了我们天文技术的一个改进。
但是现在这上面还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在乌兹别克斯坦就发现了乌鲁伯格天文台,它是一个半圆形的,那么里面也是一个很大的圭表测影的这么一个原理。当时郭守敬所引用的这些东西,因为我们元代的时候疆域很大,那么他跟这些阿拉伯世界的沟通也非常多,当时这些东西是不是有东学西鉴还是西学东鉴,我们现在也不知道,这都是有赖进一步的研究,但是圭表测影基本上就是这么样的一个状态。
在古代有非常详尽的关于圭表测影的记载,那么详尽到什么程度?就是左边的这两个是西汉的圭表测影,右边是东汉的状态。从西汉到东汉,大家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就是我们在史书里是有明确的二十四节气的影长的,它是用数值化的方式来表示的。比如说某某节气影长几尺几寸,然后甚至是到几厘,它是精确到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用数值方法把它画到上面。紫色的线实际上就是一个理论的计算值,那么蓝色的线就是史书里记载的值,西汉的这两本史书里,一个是《周髀算经》,一个是《易纬·通卦验》,这些东西都是在东汉以前的这些书,这些书籍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两个里面的记载,它明显是不符合我们实际观测的,为什么?除了冬至、夏至、春分、秋分这个基本点之外,其他的点都是线性变化的,而实际根本就不是线性变化的。我们也不是说古人没有做观测,而是说他是依照他自己的一种宇宙观来构建的这个东西,他认为必须要有一种数学方法能够让这东西可以去算,那么这个数学方法是什么?是等差数列。那么从东汉以后,我们看到从《续汉书》和《元嘉历》的这些记载里面,明显可以看到它跟实际拟合得很好了。
所以当时我在做硕士的工作的时候我就在做这一块,他们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东西?实际上就是在汉代的时候有一个“浑天说”和“盖天说”的争论,这种宇宙观的争论实际上对人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大到以至于你明明知道这个东西是错的,你还要想办法去维护它。实际上在科学史上这样的案例也屡见不鲜,有些科学家已经发现了这些东西了,但是他不敢相信这个是对的,于是就错过了第一发现权。这些东西非常多,在我们的古代实际上也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些东西,从东汉以后慢慢地这种观测技术就越来越进步,但是实际上“浑天说”和“盖天说”的争论是一直延续到唐朝,从唐朝以后慢慢地就落定了。一行做了大量的观测,包括我们后来的郭守敬“四海测验”,通过这些天文大地测量,慢慢地我们对这些东西越来越清晰了,也没有原来的那些谶纬之术的这些东西了,但是在汉代的时候这个还是很明显。
除了刚才的这种显著的变化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这种变化也很有意思,比如说像《周髀》的影长是从哪来儿的?《周髀》说冬至影长是一丈三尺五寸,夏至影长是一尺六寸,跟其他所有的这些影长记录都不一样。我先讲一点题外话,当时在做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从冬至、夏至的影长来看,从东汉一直到唐代就《大衍历》是唐代的,后汉的《四分历》实际上是东汉开始的,从东汉实际上到唐之前就是在《大明历》的时候,冬至、夏至影长是不动的。那么其他的二十二个节气的影长都在变化,越来越准,这个是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冬至、夏至影长不变。也就是说,虽然说最后“浑天说”相比“盖天说”来说它可能更准一点,它是更符合我们实际观测一点,但是它也有它的理论要维护。它认为冬至、夏至我引用的是《周礼》里面的东西,我也是周公的正学,所以这冬至、夏至我不能动,别的地方我观测完了,我发现不准了我就改,这些数据是不能改的,这也反映了同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当时觉得很蹊跷的就是《周髀》的影长,它的影长和其他所有的影长都不一样,而且影长的数值很大。实际上通过冬至和夏至的影长,它是一个三角函数的关系。很简单的一些天文计算,我们就可以得到两个量,一个是黄赤交角,还有一个就是观测地纬度。那么黄赤交角有一个长周期的变化,通过黄赤交角我们可以大概往前回推,去估算它的年代。当然这个并不是非常准,因为黄赤交角变化很慢,而且这些东西任何一个系统误差都可能让它变得很大。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大概地去估算,在千年的这种量级上,应该说它不会有太大的误差。但是如果说《周髀》是周公所做的,是在河南这个位置,是在公元前几百年或者是在这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观测的话,实际上我们回推回去就不能验证它。
在钱宝琮先生他们原来提出的这些论文里面都曾经提出了一个问题,但是他们解决不了。因为其他的像《周礼》这些数据大概算完了基本上都在河南附近,就是观测地的纬度,那么时间距今大概都是2000年左右,基本上问题都不是太大,汉代往前春秋战国基本上都是这个时候。但是《周髀》的问题就大了,因为《周髀》算下来的话,距今大概得三四千年,它的纬度也不在河南,它在比河南纬度更高,实际上是在山西南部了,就是在运城那一带了。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他们不知道,这些天文学家也不知道。一直到我们开始做陶寺之后,我们就在想,它是不是有可能有别的文明,并不是从这时候来的,而是从更早的文明继承下来的,也有这种可能。于是我们当时就开始往陶寺那个方向去想,毕竟它的纬度更高,它的年代也更早,但是现在它跟陶寺不一定完全能契合,因为我说它有一定的误差,但是至少这个问题我们指向了陶寺,就是在陶寺时期有没有圭表测影。
应该说在这之前我们也没太敢想过这个事情,正好考古学家当时也提出来这个问题,他们曾经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漆杆,他们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我们当时就认为有可能是圭尺。那么这个就是漆杆,叫ⅡM22:43它的编号,它是在陶寺中期的一个王级大墓里发现的,就是当时王级大墓,非常深。这个漆杆很奇怪的,它是立在大墓的东南角,然后所有的陪葬品全部都是平着放的,但是这个漆杆是立着放的。一个王级大墓,所以这个里面除了尸骨之外还有大量的一些玉器,然后很多宝贝都是这样的。当时漆杆被发现就像右上角那个图,实际上它已经完全都风化了,因为它是木质的,它上面刷的是这种漆器。风化了之后,我们仍然可以大概地判断出它的形制。应该说发现当时也是挺幸运的一个事情,因为考古学家的工作他们一般是打一个探洞,大概地看一下地层,然后就找农民挖,挖差不多了他们再上手。但是那时候农民刚一挖,当时山西队的何驽他比较细心,一下就发现了说这里面不对,可能有东西,于是就开始自己清理,最后发现了竖着的这么一个东西。虽然发现它顶上已经有一部分被铲掉了,所以我们到现在不知道它距离地面究竟有多高,它的全长是多少,但是铲掉的部分也就不足十厘米,所以这块也是有一个残长的。
这个漆杆我们就把它复原出来,因为时间太长久了,所以它中间有一部分已经被压弯了,再加上水浸等等各种各样的。但是从一些断的截面上,我们仍然可以大概地判断出它原来可能是两个薄的这种小木片用细绳捆在一起的。完了之后它的残长大概是170多厘米,当然具体多长,我不知道。像那边灰色的,当时发现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中间有一部分是已经完全损毁了,是看不出来的,剩下的部分它是这种一段一段的,就是说一段粉条,一段绿色,一段粉条,一段黑色,是这样的。首先它很漂亮,它就很像一种礼器,其次它的这些粉带是不是有什么天文上的这种功能我们也不知道。下面是整个它最后取土取出来,现在这个保存于考古所山西队的侯马工作站,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保存的。当时给我们看,我们的切入点,就是说它中间有一个很奇怪的一点,就是大家看到这一点,它跟其他所有的连续性是不一样的。这一点是不是有可能是一些天文基本点?我们当时就假设它是夏至时候的影长来进行计算。
那么这个杆怎么用也不知道,因为冬至的影长显然要比它长得多,冬至的影长大概核算下来得有三米多,夏至的影长基本上是在这个位置。那么经过一些比较精密的计算,后来发现确实因为一开始的测算,它可能是在“六”那个位置了,后来更仔细测算一下,它可能是在“七”的位置,因为再考虑到岁差这些影响。我们当时提出来两种可能性,一个是平移,就是我观测完了以后再往这边去移,当然从观测的角度来说不是太简单,比较麻烦。还有一种就是翻杆,翻杆就是我把表立在这儿,然后我把这个圭铺在这儿,当然如果影长超过这个圭,我只要沿着这个点再一翻打到那边,我就可以测出它这个点是多少。这也是一种办法,相对来说要简单得多。我个人是比较支持翻杆,后来我们也做了很多的测算。我就推算,如果说它是翻杆来测影的话,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头上是有一个粉红带的,头上粉红带肯定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是什么?我猜测它是冬至的影长。那么正好翻杆过去之后,两个长度相当于冬至影长,我们就推算出它的残长应该是不到10厘米。我推算出它残长大概是3厘米左右,如果它残长是在3厘米左右的话,它翻过来之后正好两个长度是一个冬至影长。在夏至的时候,它大概就是在“六、七”那个位置。其他的这些线,因为它的线更多了,那么其他这些线应该说它也对应着大量的影长,那么这些影长又可以换算为日期。经过后来我们一系列的测算,其中很多日期和陶寺无法解释的这种狭缝的日期是可以对上的。
那么这个结论应该说就比较大了,就是说陶寺当时发现的日出历的观测系统它不是孤立的,它还有其他的证据。因为我们现在从《尚书·尧典》里可以知道,在尧的时候“尧命羲和做天文观”,然后他们观测了四仲中星,这些事情我们都是清楚的。所以现在我们初步地把陶寺这个东西,一个是它日出历、地平历这样日出观测的观象台的发现,一个是它当时有了圭表测影,还有一个就是当时它有一些简单的恒星观测。
应该说这些结论加起来就相对来说比较完整了,对我们整个陶寺时期的天文的文明以及我们整个中华文明的一些起源。应该说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难接受的一个,就是我们原来觉得在四五千年前可能什么都没有了。如果说当时已经到了这种程度的话,天文应该说在当时已经是非常完备的一个系统了。它如果那时候有了圭表测影,那么观测日出方位是简单得多的,因为圭表测影第一它是数值化的,第二它是可以携带着走的,如果你通过圭表测影可以来和你的地平历的观测相印证,那么我们讲它这个文明就已经从一个地域性的文明变成了一种世界性的文明。因为你可以拿着这个表走到更远,你的统治的范围就会更大,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你这一小块。所以这个也和陶寺后来又发现的这些工程遗址和这些东西都是互相印证的,也就是说当时的文明的发展状况可能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它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强盛的状态。去年年底考古学家发现了陶寺的宫城(2017年继续扩大发掘面积,基本廓清了宫城城墙堆积、结构、年代、发展演变等问题。——编者著),也就是说他们还有紫禁城的这一层城墙。他们挖城墙又发现了阙门,也就是说城墙的门跟午门前面的阙门是一样的,它是一种礼节性的门。所以现在还有很多的东西等待我们去发现,应该说很多文明的东西是远远超出我们原有的一些想象。
2010年的时候我们就做了这个东西进行了复原观测,然后事实也和我们的估算是比较相符的,非常有意思。
这个是在后来又继续的又有一些新的发现,因为圭虽然发现了,可是表还没有。后来在跟考古学家进一步地沟通过程中,他们就说有一个老先生高炜,他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就在陶寺工作,说他曾经发现了一个木棍,这个木棍也没人知道是什么,就扔在一边了。我们就把这个木棍拿来研究,但是对于考古来说,他一直没有公开发表所以原来也没有引用。他们现在刚刚出版78—85(年)的发掘报告,应该说是比较缓慢。这个木棍非常有意思,它的编号是M200,长度大概是2米1左右。这个木棍就很有意思,首先它是圆形的棍,其次全棍通体全部是红漆,一头尖,一头平,非常符合我们所做的表这种观测。
课程简介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黎耕教授作了本次学术报告,报告主要围绕我国的考古天文学进行讲解。
首先他简单介绍了关于考古天文学和天文学史的一些基本知识,指出中国天文学史前期的研究主要是从文献资料中查找证据,在21世纪之后才与考古学有密切的合作,从考古遗址中探寻天文学的奥秘。
接着他以陶寺遗址的古观象台和圭表等考古发现为例,展示了古人对天文知识的认识和利用。科学家认为陶寺观象台是一个地平历系统,通过复原,地基上呈现的是一根根柱子,柱子间的狭缝很窄。在某些特定的节气,太阳会从某个狭缝升起来。目前狭缝所对应的确切时间还没有被全部研究出来,有待进一步探索。陶寺观象台的发现,对考古天文学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有学者认为这标志着中国考古天文学的诞生。
除了观象台外,陶寺遗址还发现了独特的天文仪器——漆杆。经过研究论证,科学家认为这是当时测影所用的圭尺,圭尺和立表组合测影可用于制定历法和领土幅员测量。
关于圭表测影,黎教授结合自己早期的研究方向,对中国圭表测影的历代发展及圭表的作用和象征意义等进行了介绍。
最后,他还就文化自信进行了论述,并对大家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解答。
(视频拍摄于2016年)
- 什么是考古天文学?
- 中国的天文学研究状况是怎样的?
- 与天文相关的一些考古发现
- 天文学对古代的城市规划有什么影响?
- 陶寺观象台的狭缝有什么奥秘?
- 陶寺观象台的发现之于考古天文学的意义是什么?
- 什么是圭表测影?其历代发展是怎样的?
- 什么叫天文尺?
- 文献是如何记载周公测影的?
- 郭守敬在圭表测影方面有哪些成就?
- 为什么有些文献记录的测影结果与实际观测存在明显差距?
- 《周髀》的影长从何而来?
- 陶寺时期有没有圭表测影?
- 陶寺漆杆使用方式的猜想
- 陶寺出土的被推测为测影用的表在形态上有什么奥秘?
- 中国天文的发展历程是怎样的?
- 中国天文学史上有哪几次重要的节点?
- 古代天文学有哪些用途?
- 从天文学角度解释“中”的意思
- 圭与分封制度有什么联系?
- 为何陶寺圭表不朽?
- 陶寺是什么时期的?
- 为什么陶寺象征权力的器皿是圭表而不是中国古代常见的青铜?
- 天文学中的指向线会以什么形式存在?
- 什么是“地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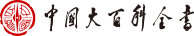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8139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813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