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先生与《春秋》“五情”说(下)
皮锡瑞在《经学通论》里头就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他说经和史是不同的,“分别甚明”,是分得很清楚的,所以读经的不能够用史法绳《春秋》,修史的也不应该以《春秋》的书法作为史法。因为《春秋》根本不是一般的历史,它是经,所以钱先生就没有把这个弄清楚。
好了,我们再看“尽而不汙”的例子。其中的例子是天王求车,鲁桓公十五年《春秋》说,天王使家父来求车,派这个家父,这个大夫,到鲁国,要求鲁国把这个车贡献给周天子。《左传》就说,它说,天王使家父来求车是非礼也,不合于礼。因为诸侯不贡车服,诸侯不应该把这个车跟服饰进贡给周天子。他每年都有进贡,所以天子不应该私求财,另外再问这(些)诸侯拿财物,那是不对的。所以,周天子做事情不对,不合于礼,那么记载的时候也要如实的,因为对这个整个礼法影响太大了,如果周天子也不守礼,那么就会崩溃,礼仪就会崩溃。由于天子非礼而动,史官就直书其事,就把这事情如实地记载,不加以隐瞒。所以记载的时候所有事实都在里头,没有汙曲。
那么第五情就是“惩恶而劝善”,就是惩戒恶人,奖励、奖劝善人,凡是好的,善名必书,好的事情一定会记载,做了坏的事情就一定也记载。最后(的)目标就是为了惩戒恶人,奖劝善人。
其中一个例子,书齐豹盗,齐豹不写他的名字(记载的时候不写齐豹的名字),只是写“盗”,“盗”是地位很低下的人,但是又犯了罪,才说这个盗。这个鲁庄公二十年《春秋》经,它说当年秋天,“盗杀卫侯之兄絷”,盗是谁呢?它没有说。就是盗,就是一个地位很低下的,而且犯了罪(的)人,杀了卫侯的哥哥,这个絷。而《左传》就把事情记载得比较详细,它说卫侯的公孟絷,就是卫侯的哥哥,他狎齐豹,就(是)轻视齐豹,把他的官,司寇之官,跟他的地,就(是)圈地拿走,有事情要找他做,就把官位还有地还给他。没有事找他,又把它拿走。所以齐豹当然很不高兴,对不对?另外还有很多人对公孟絷很不满意。因为公孟絷他又不喜欢北宫喜,还有褚师圃,要把他们除掉。另外还有公子朝,他是跟襄公夫人宣姜私通,也怕公孟絷要对付他。所以大家就联合一块儿,要对付公孟絷。有一天公孟絷有事要出城了,他们就埋伏,把公孟絷杀掉。这个事情到了鲁昭公三十一年,《左传》就解释为什么齐豹不记载他(的)名字,齐豹是魏国的司寇,司寇是很高的官,是守嗣大夫,是能够世袭的大夫,但是他所做的事情是不对的,作而不义,不对的,那么记载的时候就用“盗”。一般那么高地位的官应该记载他的名字,但是《春秋》为了贬抑、贬低齐豹,就不记他的名字,记载的时候写盗。其实齐豹他想(让)史官把他(的)名字记下来,那么后世就知道,他是不怕这个强大的势力的,虽然公孟絷那么强大,但是他不怕,他要把他杀掉,他想把他的名字留在历史上。但是(《春秋》)不记载他的名字,只是说有一个地位很低下的人杀了卫侯之兄絷。所以这个盗是地位低下而有罪,那么《春秋》偏偏就用“盗”这个名称来记载,所以我们看,《春秋》是这样子,它最重视的不是记载那个事实,而是为了褒贬。
钱先生在《管锥编》里头,他有一些事情做得很好的,他就把“五情”分为“载笔之体”跟“载笔之用”。杜预本来是把“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是平列的,是把它一块儿列出来,其实是不对的。竹添光鸿已经指出来了。他说,杜预(把)“五情”平列为五体是不对的。就是前面四个,前面的四情就是“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其实最后的目的就是为了“惩恶而劝善”。所以钱先生也有同样的看法,他就用前面四情,“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就是做载笔之体。那么第五情,“惩恶而劝善”,他认为是载笔之用,说法跟竹添光鸿所说的大致相同,就(是)“五情”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分为三层来看。“微而显”“志而晦”主要是写字面的效果,“婉而成章”“尽而不汙”其实是说书写的态度,“惩恶而劝善”是说记载的作用,作用就是惩戒恶人,奖劝善人。(这)三方面不一定是互相地排斥的,比如说书齐豹盗,这个记载是可以归入“微而显”,你去看盗,盗是谁?没有《左传》,你根本不知道,你看《春秋》,盗是谁,你根本不知道。“盗杀卫侯之兄絷”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它是“微而显”,它背后的义理是很显著,但是它字面(的含义)是很不清楚,但是也是“尽而不汙”,就是把这事情如实地记载,不为这个齐豹隐瞒,隐讳,也可以归入“惩恶而劝善”,就(是)惩戒恶人,这个齐豹做得不对,就惩戒他,他想得到不畏强御之名,想把这名字留在历史上,偏偏就不给他,就是说盗。
好了,“五情”,我们刚才说了“五情”其实主要是经学的观念。钱锺书先生就以纯史学的观点来评论《春秋》“五情”,那是不对的。刚才也说了,钱先生认为“五情”是古人写历史的时候心向神往的楷模,但是《春秋》达不到,说“《春秋》实不足语于此”。刚才也说了,“五情”本来是《左传》引用君子的话来赞美《春秋》的,他说《春秋》之称,“非圣人孰能修之”,不是圣人,谁能够写那么好,是赞它的。但是钱先生说“《春秋》实不足语于此”,达不到“五情”的标准,所以刚好是相反。关键在哪儿?其实君子称赞《春秋》,用“五情”来称赞《春秋》,它的标准不是钱先生心里头的,所谓写历史的时候心向神往的楷模,它不是用历史观点来说的。如果我们用史学观点来看,就“梁亡”这句话,这个记载,就是断烂朝报。《春秋序》称赞“五情”,主要是因为“文见(现——编者注)于此”。你看我用文字去这样记载,但是“起义在彼”,背后有一个义理,能够“发大义”,能够阐发大义,能够指导行事,能够以正褒贬。我们再看刚才我们引用过的例子,就是说郑庄公用璧玉问鲁国借这个许田,其实是交换,那么交换,因为这个事情不对,所以它加以很婉曲地记载,说借,只是借,但是不是事实,它记载(的)根本不是事实,所以《春秋》记载的不是如实的,不是一般历史的记载。那么另外刚才也说了,就是周平王驾崩的时候,本来是三月二十四日驾崩,它偏偏写是三月十二日,那么重要的事情,天子驾崩,也不如实记载。所以钱先生以纯史学的观点来评论《春秋》,这个是没有掌握《左传》里头引君子的话来赞美《春秋》,还有杜预《春秋序》(《春秋左传集解》序)里头也赞美这个《春秋》,钱先生没有掌握其中的关键。我们看杜预的《春秋序》,他说“推此五体”,就(是)“五情”,来看这《春秋》经跟《左传》,那么,“王道之正,人伦之纪”都已经全在里头了,那么它所用的就是经学的观点,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君子就是赞美《春秋》,说“非圣人孰能修之”,他也是用经学的观点。
好,最后我们谈钱锺书论《春秋》“五情”与诗学,他把这“五情”跟诗学拉上了关系。(侯)敏泽先生他就谈到,钱锺书先生在1980年就跟他说,汉代对后世的文学理论,影响最大的不是《诗大序》,而是这个《春秋》笔法。受到钱先生的影响,所以敏泽先生在他的书里头,他就设立了专节来谈《春秋》笔法对后世文论的影响。周振甫先生也是在他的书里头也设立专节来谈这个《春秋》笔法。近世以《春秋》笔法谈诗的,就由钱先生开始。那么钱先生他在《管锥编》里头说,古人谈《春秋》的,大多数赞美它,说它辞约义隐,因为文辞简约,用很少的文辞,而且它要表达的意义也是比较不清楚的,比较含蓄的。那么他说对于这(种)说法,其实没有把整个事情讲得清楚,因为《春秋》时候要记载是很麻烦的,所以行文的时候不能够不简约。古人没有纸张,用漆书写在竹简上面是很麻烦(的),所以他也引用章学诚(的话)说,用漆文写在竹简上面是很繁重(的),所以文辞要简严。所以《春秋》要“微”,要“晦”,要“简严”,是历史条件的关系,是书写条件的关系,没办法,不是如此。那么杨万里他在《诚斋集》里头就引,“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这跟《史记》称这个《国风》所说的两句话,他最后就说,就是《诗》跟《春秋》“纪事之妙”也。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看,钱先生说,《春秋》文字简约,是因为漆文、竹简繁重不胜举之故。但是沈玉成先生他又有另外一种看法。他说,你看,《春秋》之后不久,就有《左传》,有《国语》,《春秋》《国语》,它们的记载是很详细的,它一定有所根据。所以在《春秋》的时候,应该已经有很详细的记载,有些记载很详细的史书不一定全都像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春秋》那么简约,就对这个事情有两种看法。另外一方面,赵伯雄教授他就认为纲要式的大事记是春秋时代各个国家的史官记事的常法,是一般的方法。那么赵先生的说法跟沈先生是不同的,赵先生只是说纲要式的编年的大事记是当时各国史册记事的通例。至于当时是另外还有记载详细的文字,赵先生其实也没有把它否定。我们再看钱先生,他说,“《春秋》文字简约”,“微”“晦”“谨严”是因为受到书写的工具的限制,没有办法不简约。后来的人不知道,就说《春秋》书法是史家的楷模,又用史笔跟诗笔相提并论。
杨万里就引“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这四句话,认为这个是表明“《春秋》纪事之妙”,就把它跟唐宋的诗词来相提并论,认为《春秋》跟诗词都是“言有尽而意无穷”。杨万里说太史公,《史记》里头说国风是“好色而不淫”,小雅是“怨诽而不乱”。又说《左氏传》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这个就表明《诗》(《诗经》——编者注)与《春秋》“纪事之妙”,他又引用(宋)陈克(的诗)谈到,唐玄宗把他的儿媳妇寿王的妃据为己有,把她抢走,做自己的妃。(这两句诗是)“汗简不知天上事,至尊新纳寿王妃”。一般的历史记载不知道高层的那些事情,其实现在的皇上是把寿王的妃子纳为己有。那么这两句的诗句是“微”吗?是“晦”吗?是“婉”吗?是不污秽吗?其实比李义山(李商隐),李商隐的更好。李商隐说,“侍宴归来宫漏永(夜半宴归宫漏永——编者注),薛王沉醉寿王醒”。那么这两句诗,可谓“微婉显晦,尽而污(矣)”,李商隐这两句诗出自他的《龙池》。他说,“龙池赐酒敞云屏”,就是唐玄宗在龙池宴客,赐酒,就(是)很多屏风又很华丽。那么音乐呢?“羯鼓声高众乐停”,就是很多胡人的音乐,特别地多。宴会完了,“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到半夜,这个宴会完了,回到宫殿里头,寿王因为他的妃子给他的父亲,给玄宗抢走了,所以他睡不着,整个晚上,整夜听报时。其他人呢?包括薛王就喝得昏昏大醉,但是寿王又整个晚上睡不着。他没有说这玄宗把他的妃子抢走,但是就用这两句话,特别后面那句,就是说“寿王醒”,就是说整个晚上他睡不着。所以罗大经就说这首诗是“词微而显,得风人之旨”。吴乔就说,它是有“含蓄不尽之意”,很含蓄,没有直接地说唐玄宗不对,但是他由寿王的表现,就是说他睡不着,表明了整个事情。我们看杨万里,他在“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里头就取了“微”“晦”“婉”跟“污秽”来谈陈克的诗句。那么其实他有些以偏概全,而且他所用的也不是这四情,就(是)“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这“四情”的原来的意思。宋人,杨万里是在宋代,当时就是这样子,宋代文化它比较重视和合集成,所以在学术、在文艺上面就有这种会通的风气。宋代诗学就是显现这种的会通化成的一种现象,所以他谈诗学的时候就会多层面地借镜、融通、化用其他的学科,经常做“出位之思”,就(是)从不同的学科中间可以相融之处就加以引申。《春秋》学在宋代,它是显学,当时研究《春秋》学的人很多,所以《春秋》笔法在当代文风是很有影响的,这个书画笔记有很多都用《春秋》书法来谈诗,所以杨万里引“微而显”等等,就表明《春秋》纪事之妙。又举唐宋的诗词作为例子来谈论它,认为《春秋》跟诗词都是“言有尽而意无穷”。
钱先生根据杨万里的话,就说《春秋》“五情”是跟诗学有关,但是我们再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其实跟诗词“言有尽而意无穷”,它的性质究竟是不同的。我们看杜预,他所举的很多例子,其中刚才谈到的有璧假许田,有天王求车,有书齐豹盗,都是没有诗意、没有诗味的,你看就是说用璧玉送给鲁国,问他借许田,跟他交换土地,有什么诗意呢?那么周天子到鲁国要求他进贡车马,有什么诗意呢?那么齐豹杀了这个卫侯之兄絷,那有什么诗意呢?都没有诗意,对不对?所以什么“言有尽而意无穷”,这个其实是两码事。我们不可以用《春秋》跟诗相比。谈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
课程简介
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序中提到《左传》赞誉《春秋》的“五情”说,即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他认为“微而显”是辞微而意显,即文词不是很清楚,但是它背后的义理很显著,举例“梁亡”加以说明;“志而晦”表示很简略地把事情记载,“三会不地”的记载即是证明;“婉而成章”,很委婉的屈曲其辞来写成篇章,“璧假许田”的做法有悖于当时的礼法,所以记载时很委婉地说是“假”;“尽而不汙”就是把事实照实来说,尽其事实而不加以汙曲,举例“天王求车”,说明就算天子做了错事,也要如实地记载;“惩恶而劝善”,即惩戒恶人,奖劝善人,“书齐豹盗”就是很好的证明。
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认为这“五情”是古人写历史时心向神往的楷模,但是用这个作为标准,《春秋》实不足语于此,也就是说,《春秋》没有达到“五情”的标准。香港大学的单周尧教授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分析,认为《春秋》是经,而不是史,钱先生用纯史学的观念来评价《春秋》是存在问题的。
钱锺书先生还在《管锥编》中将“五情”分为“载笔之体”跟“载笔之用”,单教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五情”分为“字面的效果”“书写的态度”“记载的作用”三个层面。另外,在《春秋》笔法、《春秋》“五情”与诗学有关的这一说法上,单教授也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视频拍摄于201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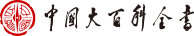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8139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813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