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的视角看比较文学(一)
大家标题看了,我这个标题稍微有一点改动。原来是想设定“日本的视角”,但是考虑到我又不是一个纯粹的日本人,所以“日本视角”——作为一个代言,可能有点——从角度讲,不够完整。所以我想,我作为一个日本文学的研究者,然后又是中国的立场,这样的话从“东方的角度”,说合适也不是完全合适,因为东方整个概念还是很大。这一点我觉得倒并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就是说,今天我们要看这两本书,是吧?上半场主要是讲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结合这本书做一些个案的分析,下半场讲《上海》。
我们先来看安德森。我下面有提示的关键词,里边有一个“重建研究者的主体位置”。这个是不是就和昨天谢老师讲的内容,有一种“转”了?这个“转”在什么地方?听了昨天的讲座,我们就感觉每一个人都是比较文学研究者,是吧?按照日本的研究领域或者研究学界的理解,进了研究生院,是吧?进了研究生院的,那么硕士生、博士生都已经开始算研究者了。所以大家作为研究者从这个角度去考虑,那么我们会从谢老师那里得到一个非常总体的、坚实的、充满信心的这样一种学术的底气。
今天我这个“转”,可能稍微有一点不同,也就是说,昨天你们获得那么坚实的概念,今天我要稍微给它动摇一下。
这个“动摇”我们看一下,这是前面红的,这是第5页,从这个《想象的共同体》里边引的一段话。这里面说:“换言之,和大多数其他的主义不同的是,民族主义从来没有产生过它自己的伟大思想家:没有它的霍布斯、托尔维尔、马克斯或韦伯。”这些都是社会学的名家了。这就呈现一种空洞性。关于民族的研究,作者安德森认为有一种空洞性,看到“空洞性”几个字,我就联想到比较文学是不是也存在这种问题?没有大的比较文学这种理论家或者思想家,是吧?这种空洞性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要提出来?这意味着,安德森能写出《想象的共同体》,那么比较文学同样为大家留出了一个广阔的有待耕耘的空间。这是第一点,我想要说的。
那么空洞性和重建研究者的主体位置,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看一下。这是第6页印的一段话,他首先对民族民族——民族原来有很多人下了很多的定义——安德森他又重新给了一个定义。这可能跟安德森他自己作为研究者主体定位有关系,因为他自己出身,是吧,他的出身,然后接触异文化的这种丰富的经历,所以他对民族的理解就格外地和一般人不太一样。他的定义是什么——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它为什么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我们不认识每一个中国人,是不是?这两天我们聚到一起,大家彼此可能才开始相识,即使同样在上海、在上海的周边。从来他们没有相遇过,甚至这一辈子都没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尽管中国十几亿人,我们不认识其他人,但是我们知道有十几亿人和我们共同生活在这片国土上,是不是这样?
那么,让你有这样一种联想、一种感觉,这种根据从什么地方来?下边说“民族的本质”在于什么——“每个人都会拥有许多共同的事物”。还有一个,“同时每个人也都遗忘了很多事情”。我不知道在讲座之前,我给大家提供书目之前,有多少人看了这本书,看了之后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现在重读你会又有什么样的联想?比方说,“拥有很多共同事物”,这个容易理解。比方说,中国人都用筷子,是不是?然后“爆竹一声旧岁除”,马上新年要到了,是吧?我们都拥有这样的一种共同事物。美国人他也许不会过中国的春节,对吧?但是,“同时每个人也都遗忘了很多事情”就不太好理解。这个指的是什么呢?在安德森提出的一个问题。那么,尤其“共同遗忘”,我觉得在以往的比较文学的视角,我们经常会忽略这样一个视角。今天读这本书,其实我的用意是在于,我们不是把它作为一本社会学的经典来读,是从我们比较文学的立场来看这本书,重读的话,这里面会提示什么样的启示?
再看下边。也就是说,一切共同体都是想象的。那么,区别不同的共同体的基础,是什么呢?不是这个民族是真的或者假的,而是他们被想象的方式,其实这“被想象”也就是想象了。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日本人,每一个人都有关于自己民族的想象。结合我们比较文学视角来看,我们关于民族的想象,对方他者关于民族的想象,如果站在比较文学的立场去看的话,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种关联性,它比喻成一种亲属性,是以特殊主义的方式被想象的。这些都值得思考。比方说,有一些原始部落,他们没有表示“社会”的词。中国近代之后才出现“社会”这样一种说法。那么古人他是不是关于民族,他就没有想象了?也有,想象的方式不同。
除了安德森提到的这些,我觉得关于民族的想象,我们经常能够切身地感觉到的,还有语言、文字、服装,最重要的肤色。我们一看,尽管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不大容易区分,但是可能蒙古族的或者蒙古人,就比较容易好区分了,阿拉伯人更容易区分,西方的白肤色,是吧?法农不是写过一本非常有名的《黑皮肤,白面具》(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是吧?这些我觉得都可以作为比较文学的经典的东西,我们来理解,是吧?
下边他又接着说,这是6到7页,说“民族被想象为有限的,即使最大的民族,就算他们涵盖了十亿个”,我估计他写的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想象在中国,“即使这个民族有十亿个活生生的人,但是他们的边界,还是有边界的”。中国历史的边界它一直在变,尽管变来变去还是有限的,它不是无限的。“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把自己想象为等同于全人类。虽然在某些时代,基督徒确实有可能想象,把地球作为一个信基督教的一个星球,然而,即使最富于救世主精神的民族主义者也不会像这些基督徒一样梦想有朝一日,全人类都会成为他们民族的一员”。民族是有限的,它总是有边界的。
这个边界,我就想昨天我们讨论的问题,关于比较文学,谢老师给了很多很多这种精彩的定义,很明确的。那么如果让我来谈“比较文学是什么”的话,我会启承转,我稍微转一下,我认为比较文学最关键的一个特征,就在边界。
我们怎么划分?为什么要搞比较文学?大家知道,比较文学就是近代之后才兴起的,谢老师给的数据里边是1816,用了这个字,今年是2016,正好200年。那么近代之后,由于近代民族的兴起,民族,国族,国家和民族是捆绑在一起的,经常打包捆绑在一起,它就有一个边界。
那么日本文学史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中国文学史什么时候开始有的?比较文学不考虑这个问题吗?要考虑,是吧?中国的第一本文学史是晚于日本的学者的,并且日本学者在明治初期就已经写过中国文学史。由于他们积累,所以比较文学是因为国别史越来越多,国别文学史越来越多。
那么国别史它越来越多,它意味着什么呢?边界,意味着我想是这样。一个作家,李白,他也许就在中国境内活动,但是到近代,随着大航海,那么越界的活动越来越多。一个人他并不是一定要把自己的活动限定在一个界限之内,一个作家同样如此。这里面就牵扯到我们有一些同学在研究旅行的问题。近代文学当中的旅行,如果旅行是越界的,比方说郭沫若留学日本,鲁迅留学日本,作为国别文学史,你怎么写呢?他在日本这段经历,你怎么写到文学史里面?我们可以看文学史,关于这一段经历都是非常简略的。也就是说一旦划分了边界之后,一定要把作家作品腰斩了,有一部分不属于国别的他不好强调了,是吧?
比较文学恰恰就因为国别文学史越来越发达,才产生了比较文学的需要。如果说国别文学史是有界的,那么比较文学的特征在哪?它是越界的,它是跨过疆界的两头。
那么谢老师还提到一个概念,就是歌德说的世界文学。如果放到这个框架里边,再考虑“世界文学是什么”的时候,我认为世界文学是无界的。那么没有界的文学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学?也就是说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是不是一回事?我觉得从概念的角度讲,这两个不应该混为一谈,为什么?我说它是无界,因为在整个世界范围来看文学的发展,这里面就牵扯到我刚才说的研究者的主体重构、重新定位的问题。
我们想象,郭沫若从中国到日本,把他作为一个整体,不因为一个疆界把他割裂了,作家你不能腰斩他,这时候需要一种比较文学的研究。那么如果整个世界是一个疆界,现在经常流行所谓的全球化的说法,它是一个疆界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看文学怎么看,或者说什么样的课题才是世界文学研究的课题。
我想,世界文学的无界并不是说真的没有界,只不过那种占有支配地位的视角、立场,它丧失了它本来的这种优越性。更多的我想有一些现象,比方说一种传说、一种传播,像《共产党宣言》,它在整个世界传播的范围,就需要一种世界文学的视角去看。是吧?它传播到不同的领域,引发不同的反响。这个时候你用有界或仅仅用越界,是探讨不清楚的。这个是我理解的,如果是世界文学它的特定的课题和比较文学如果做区别的话,那是不是可以这样考虑。
顺便就联想到所谓的康有为,他是提过一个非常著名的概念——“大同”,从古典里面挖掘出来这样一种思想。结合刚才说的安德森的民族概念,我想康有为想象的“大同”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大同”?这种“大同”在我们观照近代、做近代比较的时候,那么中国人心目中那种“大同”跟“民族”有多少重叠,有多少差异呢?不考虑这种差异的话,仅仅用“民族”、用“国家”这种词,我想近代的人和我们现代,用的肯定是不一样。所以,重建研究者的主体,可能也包含了这样一种回到现场的意义。
回到那个现场,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现在我们都用“文学”这个词,“文学”这个词大家都用,那是大家知道。近代最早开始用“文学”的时候,那种语感是什么样的语感呢?中国古典文学它不用“文学”这个词,是吧?那个时候是有诗、有词、有曲,还有文,还有赋。赋现在基本上算消亡了。那个时候是用这些来支撑我们现在说的文学。
所以近代最初的,我在日本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大概有二十多年了。我当时做的研究就是考察“文学”这个词最早什么时候开始,不光在日本,在中国开始用的。日本学者铃木修次的观点,他认为是日本的启蒙思想家西周最早用的这个词。
这是我当时在日本读博士的时候我思考的一个问题,也是像大家一样,在上课的时候做研究发表,那就开始做了这样一个小题目,但是越做越大,收不住了最后。
因为什么?牵扯的太复杂。首先西周你去看,那么比西周更早的用例,你到哪去找?如果让你找,你去什么地方找?这里面就牵扯到一个“接着说”的难度的问题。
当时我的思路是因为看了一些近代传教士的东西,在华的传教士。他们翻译,当时有一本杂志叫《六合丛谈》。《六合丛谈》是在上海办的,传教士办的,也是中国近代的第一本月刊杂志。这个杂志的创刊号上就出现了一个,并且是第一篇的文章。出现了什么?《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这样一篇文章。传教士是艾约瑟。那个时候,翻译得很有意思,我想可能是传教士和中国的学者共同的翻译,所以经常会写“谁谁谁述、谁谁谁记”,是吧?那么这里边,传教士是艾约瑟,一个非常有名的传教士,在华50年,最后他死的时候是埋葬在北京了。这样一个人物,他把毕生几乎都献给中国了。他的助手是谁呢?大家也非常熟悉的一个近代人物——王韬。王韬办《循环日报》,中国人办的第一份日报。那么最有意思的,我跑到东洋文库那个藏书楼,就把《六合丛谈》找出来,我还特意看了一下。一般人不太注意,它那个书已经很旧了,封面用透明纸重新修补了,透明纸遮住的地方,就是英文的目录的对照。也就是说它不光是中文目录,这里边还有英文,我觉得这个证据应该是算是强证据。但是光做到这一步还不够。当时我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时王韬、艾约瑟他们东西方观念对接的时候,为什么西方的“Literature”要对应中文的“文学”?因为当时他们的努力,所以我们现在有了“文学”的概念。这个我就不详细做交代了。
课程简介
李征教授从比较文学的立场,对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的关键内容进行了解读,对重建研究者的主体位置做了引导和启发。
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
民族是有限的,它总是有边界的。——引申到文学研究领域,如果说国别文学史是有界的,那么比较文学则是越界的,是跨过疆界的两头。
所有伟大而具有古典传统的共同体,都借助某种和超越尘世的权利秩序相联结的神圣语言为中介,把自己设想为位居宇宙的中心。——引申到文学研究中,需要注意语言的符号性;语言在共同体的想象中,发挥着“符号的非任意性”的作用,也就是说不是想改就能改的。
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有数以百计的人,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者去从容赴死。——为了深入解析这种关于民族的意识,李教授对“空闲少佐”的中日不同版本的文学资料、真实历史事实进行了介绍、比较和分析。
共同体所以能够成为可以想象的,语言给它划定了一个边界,但是这个边界还有它的合理性,并不是单纯语言这一个因素就能解释清楚。——对于语言的“划界”的作用,李教授以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的小说《金阁寺》中的男主人公为例进行说明,小说中男主人公说日语口吃,但说英语不口吃,正是由于两种不同的语言环境的影响。
(视频拍摄于2016年)
- 《想象的共同体》中对“民族”的定义是什么?
- 《想象的共同体》中“民族”的本质是什么?
- 区别不同共同体的是什么?
- 怎样理解民族的边界与比较文学的边界?
- 怎样理解“世界文学的无界”?
- “文学”一词的溯源
- 《想象的共同体》中关于“语言”的论述
- 史学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差异性在哪里?
- 文学为什么要作为“符号”来读?
- 怎样理解“符号的非任意性”?
- 怎样理解民族共同体巨大的激发力?
- 对穆时英《空闲少佐》出版时间的解读
- 穆时英创作《空闲少佐》小说的时代背景
- 穆时英《空闲少佐》小说的写作手法
- 穆时英为什么选择空闲少佐为小说主人公?
- 穆时英《空闲少佐》小说的故事线内容
- 日本当时对待空闲少佐的真实姿态
- 中日两版《空闲少佐》在内容上有什么不同?
- 《肉弹三勇士》与《空闲少佐》的关联
- 从“语言”的角度,怎样理解《金阁寺》主人公的口吃与不口吃?
- 怎样拓宽“比较文学”研究的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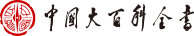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8139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813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