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的视角看比较文学(二)
还是回到艾约瑟这个,民族边界的问题。这本书涵盖的内容非常广,那么我重点把里面跟语言有关的部分,特意地拎出来。
他说:“所有伟大具有古典传统的共同体民族,都借助某种和超越尘世的权力秩序相联结的神圣语言为中介,把自己设想为位居宇宙的中心。因此拉丁文等等,包括中文,它的扩张范围在理论上是没有限制的。”事实上书写文字越死亡,它越处于死亡的状态,离口语越远的意思,那么就越好。原则上为什么?因为这样的文字人人都可以进入,它是一个纯粹的符号的事情。
在这边我也特别想提醒大家注意符号性。因为我觉得在文学研究当中,有一些学者他区分不开“事实”和“符号”的这种差异。比方,我就不提具体名字了吧,搞研究的有一些学者,他最后做出来的东西,你看起来完全就是史学的。这里面我有一个疑问,我说既然你是做文学的,那么当然你越界去做史学也未尝不可,是吧?但是你这不是抢史学的饭碗了吗,是不是?或者说你自己的本行,你怎么来守住呢?
我认为最大的特点,做史学研究和文学研究最大的或者说差异性在什么地方?史学是讲的史料,它讲的史实,去追求一种真实的还原。但是文学是符号,真不真不重要,是不是?关键就是这个符号怎么运作的问题。
昨天我也提出符号问题了,但是没有时间展开讨论。文学如果不作为符号读的话,我觉得就没读解到位。不是有一个同学昨天提另外一个问题,说假如小说里面虚构的一个人物,你去谈对他进行心理分析,这种合理性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就有这种问题?
文学虚构尽管是虚构的,但是实际上,现实当中如果把人理解成符号,是不是每个人也是虚构的?我们每一天都在通过各种各样的行为来建构自己,不是吗?阿伦特——也是社会学家,她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说“生命是一种叙事”。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我们没有关于童年的趣事的记忆,没有一些照片的提醒,没有这样一种叙事结构的话,你怎么去理解你自己的人生呢?所以人生、生命是一种叙事。我们关于世界的看法其实还是一种叙事。
所以西方研究的这种阐释学也好、叙事学也好,我觉得国内现在是偏窄了。因为,按照我的感觉,他们理解的“叙事”也许是在一个重大的层面、框架范围内,或者说涵盖了整个的人文的这样一种结构。包括理工的,是不是也是一种叙事呢?只不过它的叙事和人文的叙事,结构啊、方法啊不大一样。问一个公式,你怎么把它说明出来,不是说一看就懂,你还是要运用“叙事”。
既然叙事,我们就要进入符号的世界。进入符号的世界,我觉得假如对索绪尔的这种结构主义符号学,缺少必要的积累或者理解的话,从事文学研究,那么总会迅速地、马上就会遭遇到瓶颈。
好,刚才提出符号。这个符号我又给它做了一些发挥——文学的符号——我们要进一步思考文学的符号。
这种语言,我为什么特别关注这里边提出的“语言”的问题。因为语言它的民族共同体,想象当中、这种建构当中,它起的作用,“由神圣语言结合起来的共同体”。
中国人都说中国话,汉族都说汉族话,是吧?甚至现在网络上有很多骗子,我记得我刚刚从日本回到中国来的时候,就接到过一个骗子电话,说:“你中奖了,恭喜你!”结果,他说话的同时,你就听见外边有鸡叫声,嗷嗷的,鸡在打鸣。我一听天哪,呵呵,肯定是让我一下就想到乡下,是吧?还有他说话的方言。所以肤色能区分一个人,乡音也能区分一个人,是吧?
汉字圈,我们这汉字圈的共同的,现在我们认为韩国、日本、中国,包括以前的越南,那都是属于汉字圈。这种想象,基于文字的象形文字的想象。
当然想象在近代之后经历了很多挑战,是吧?也出现了很多分化、演化,包括像朝鲜的彻底废除汉字,是吧?中国也曾经流行过一段,50年代,走拼音化、拉丁化的道路。这些都意味着什么?在我们共同体想象的时候,这个汉字的命运。
日语和汉语也是一样,尽管我们同样用的汉字,现在汉字已经有一些不一样了,是吧?所以再强调的话,特别关键的,是说,语言在想象共同体里边发挥的作用,越老、传统的共同体,它对语言越充满了一种信心。
那个时候,这里面说异乡人,我想可能指的就是最早到中国来的传教士。明末的时候,利玛窦他们来的时候,你看那个记载,它说,“着华服”——穿着中国的衣服,“习华语”——他说中国话。那个时候传教士他采取的是一种归顺的这样一种策略。他如果不穿中国服装,不说汉语的话,我想利玛窦他不会有后来的这种成就。相反的,徐家汇藏书楼——徐光启这些人,他们在接触到利玛窦这些人的时候,我想他怎么想象的西方?是不是利玛窦他们说汉语的时候,他也会觉得很舒服?这种心里舒服,又意味着什么?
那么那里边又提到“符号的非任意性”,它不是说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的。
中国走拉丁化,喊了那么多年,最后没搞成。当初是可以理解,觉得汉字是一种阻碍,影响现代化速度。
日本明治初期就有非常极端的观点,当时的第一届文部大臣森有礼,他提出一个非常全盘西化的观点,说日语太落后,我们全都改成英文吧,把英文作为国语。
中国有没有这种类似的?如果看一看出版的书,最起码简化字,第一批、第二批,我们现在用的第二批。有没有第三批,知道吗?有第三批,实行了,有几年。大家去找,你到图书馆能找到那几年出的书,不多,还有报纸,用了第三批,非常难看的简化字。
大家可以看到,文字、语言在共同体想象当中它发挥的作用,它是“符号的非任意性”,也就是说不是你想改就能改的。
那么,体现在一种语言文字的政治的时候,像《古兰经》,阿拉伯人认为这种文字才最接近真理。西方,我想经典翻译成汉语的时候也遇到这个问题。比方说我们经常说天主教,是吧?又说上帝,最初关于究竟该译成“天主”还是译成“上帝”,有过相当激烈的争论,最后都闹到罗马教廷。
第7页也有说“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尽管共同体内部有穷有富,存在不平等,但是共同体内部的人总是感觉血浓于水,是吧?并且有数以百计的人,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者去从容赴死。这种死亡“迫使我们面对民族主义提出来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种只有短暂历史想象的,缩小了的想象竟然能够激发人巨大的这样一种牺牲、一种热情”。
作者写这段话的时候,我想他心里边肯定有很多历史场景浮现出来。当然这里边我不是特别同意“短暂”——历史短暂,因为从中国历史来看,我们宋啊、元啊,那个时候实际上这种民族的意识是很强的,它历史未必短暂。但是我认为它这一点说的是对的,就是说这种关于民族的意识,在近代迅速地扩展,跟国族、国家的观念结合在一起,这个是我们非常值得关注的这样一种现象。
那么说到这儿,其实我这里边就想提一个个案。
在日本有一本杂志叫《亚洲游学》。搞比较文学研究的人,我觉得应该关注,因为这本杂志看起来像书似的,一本书,它是定期出刊的,也有时候出这种特辑、专号或者书。总之,很多比较文学研究、关于中国的研究,在这本书里面出现的好文章非常多,大家可以去关注,叫《亚洲游学》。
这是其中的一个专号,专刊,这个专号特辑就叫《战争期间的东亚——日本与文学》,它没有说日本文学,这个措辞是有差异的。什么叫“日本与文学”呢?也就是说,它涵盖的除了日本本土之外,范围更广,包括原来的满洲国时期的、在朝鲜殖民地时代的,包括中国台湾的,都有。那么大部分更多的,是他们用日语来创作。
在这本书上,我发表了一篇文章,专号里边分了什么传媒的,还有上海的,等等,还有日本北方的、南方的,这样几大区块。我这篇文章,标题是《1932年的上海》,然后几个关键词:战争、传媒、文学。主要说的是什么?缘起在于穆时英写的一本小说,叫《空闲少佐》。中国文学研究者对这本书大概是非常熟悉的,我想搞比较文学研究,各位也应该知道穆时英这个名字,中国新感觉派的,对。但是这部小说,我就查遍了中国相关的这种文学史里边,都是语焉不详。
当时我好奇在哪呢?看这篇小说的时候,我做的比较文学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中日新感觉派”,必然要涉及这个作家,这个作品又是绕不过去的,但是我写论文的时候,说老实话,没有找到足够的资料去说这个问题。这个是博士论文做完之后,那么继续挖掘,它难在什么地方,一般的人把它理解成一个虚构的作品。但是实际上后来我查了一下,我就好奇,我说“空闲少佐”有没有这个人?
大家看到现在这个版本是1932年良友作为“一角丛书”出的一本书。这个书上写的日期,其实挺有意思的,你要仔细看这个版本的话,首先你看那个封面,然后它封面的设计图形,究竟是一个狼在吃什么,一个鹰吃什么,还是碉堡、士兵战斗的情形?总之很抽象,让你想象。这篇小说,首先版本就很有意思,后来是收到穆时英几部小说集里边,当时写完了之后是作为单行本出版的。
“良友丛书”,“良友”这个公司大家可能都熟悉。上海最有名的《良友》画报——这公司出的。我们现在要了解近代中国的这种开放的程度,很多要从《良友》画报上去找资料。那么它同时也出一些小说,这里面这套丛书——“一角丛书”里边,什么丁玲啊等等的,什么沈从文啊,他们的作品都收在里边了,穆时英的是其中的一本。
我为什么要强调它1932年出版?这个是关于穆时英的几个短篇小说,《南北极》《共同墓地》,还有《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我为什么要强调这样一部作品呢?回头我就要介绍真山青果的作品。也就是说在1932年,大家知道淞沪战役第一次——1932年“一·二八”,后来是“八·一三”战役。
那么这个小说看它的版本写的是2月,2月出版,好像是5月,字有点小,现在我看不大清了。总之大家可以想象,“一·二八”打的。后来我查,关于“空闲少佐”他那场战役是2月23日。这个小说出版,就算在5月出版的话,大家想什么速度?2月23日,空闲少佐被俘,你就算了解它整个事件经过的话,也得要点儿时间,然后再写成小说,是不是?结果那么快就出了。
这样一种出版速度意味着什么?我做这篇小说,说老实话,当时其实想的很多问题,就跟刚才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有关。现在再回头看1932年那场淞沪战役,历史已经过去那么久了,如果回头再看,再把那段历史刷新地看的话,有什么意义?我想是不是跟“共同体的想象方式”有关。
无论是穆时英,还是接下来,我要说这个真山青果,日本作家,两个人都写空闲少佐,并且都是1932年,昭和七年是1932年,他这个时间还比穆时英晚了一个月,6月的,最早是发表到《镜子》(音)这个杂志上面,写的是一个剧本,后来由日本的明治座剧团上演,搬上了舞台。
课程简介
李征教授从比较文学的立场,对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的关键内容进行了解读,对重建研究者的主体位置做了引导和启发。
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
民族是有限的,它总是有边界的。——引申到文学研究领域,如果说国别文学史是有界的,那么比较文学则是越界的,是跨过疆界的两头。
所有伟大而具有古典传统的共同体,都借助某种和超越尘世的权利秩序相联结的神圣语言为中介,把自己设想为位居宇宙的中心。——引申到文学研究中,需要注意语言的符号性;语言在共同体的想象中,发挥着“符号的非任意性”的作用,也就是说不是想改就能改的。
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有数以百计的人,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者去从容赴死。——为了深入解析这种关于民族的意识,李教授对“空闲少佐”的中日不同版本的文学资料、真实历史事实进行了介绍、比较和分析。
共同体所以能够成为可以想象的,语言给它划定了一个边界,但是这个边界还有它的合理性,并不是单纯语言这一个因素就能解释清楚。——对于语言的“划界”的作用,李教授以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的小说《金阁寺》中的男主人公为例进行说明,小说中男主人公说日语口吃,但说英语不口吃,正是由于两种不同的语言环境的影响。
(视频拍摄于2016年)
- 《想象的共同体》中对“民族”的定义是什么?
- 《想象的共同体》中“民族”的本质是什么?
- 区别不同共同体的是什么?
- 怎样理解民族的边界与比较文学的边界?
- 怎样理解“世界文学的无界”?
- “文学”一词的溯源
- 《想象的共同体》中关于“语言”的论述
- 史学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差异性在哪里?
- 文学为什么要作为“符号”来读?
- 怎样理解“符号的非任意性”?
- 怎样理解民族共同体巨大的激发力?
- 对穆时英《空闲少佐》出版时间的解读
- 穆时英创作《空闲少佐》小说的时代背景
- 穆时英《空闲少佐》小说的写作手法
- 穆时英为什么选择空闲少佐为小说主人公?
- 穆时英《空闲少佐》小说的故事线内容
- 日本当时对待空闲少佐的真实姿态
- 中日两版《空闲少佐》在内容上有什么不同?
- 《肉弹三勇士》与《空闲少佐》的关联
- 从“语言”的角度,怎样理解《金阁寺》主人公的口吃与不口吃?
- 怎样拓宽“比较文学”研究的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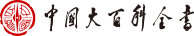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8139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813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