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诗学、认知诗学与世界诗学(二)
现在我着重地阐述我的世界诗学的构想。当然,作为中国的学者,建构一种具有普适意义的文学阐释理论,或曰世界诗学,首先就要通过对中国和西方以及东方主要国家的诗学的比较研究,才能站在一个新的高度提出自己的理论建构,否则,重复前人或外国人早已做过的事情,绝不可能取得绝对意义上的创新。因此我认为建构一种具有普适意义的世界诗学就势在必行。当然,建构世界诗学有着不同的路径,它具体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世界诗学它必须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我们都知道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题目就叫诗学(Poetics)。你看,鲍桑葵的《美学史》就叫美学史(A History of Aesthetics),他就不提西方美学史。然后一个法国学者Queneau,《世界文学史》里面他描写中国文学只有130页,法国文学多少呢?12倍,印度文学140页,就可想而知,中国文学在他的《世界文学史》当中占有的比重是非常轻的。德国的学者汉斯·麦耶(Hans Mayer),他的一本书的题目叫Weltliteratur,就是《世界文学》,但是,他凡是欧洲以外的文学他都不提,欧洲文学就是世界文学。所以可想而知,西方中心主义是非常的根深蒂固。所以我想世界诗学首先要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包容产生自全世界主要语言文化土壤的文学理论,因此对它的表达就应该同时是作为整体的诗学和作为具体的文学阐释理论。因为整体的诗学,Poetics,诗学的单数和复数都是一样的,所以我把它作为一个具体的,就叫文学阐释理论,Literary Theories of Interpretation。
第二,世界诗学必须要跨越语言和文化界限。当然,跨越语言的界限,我们都知道西方国家也有很多语言,比如从英语到法语就跨语言了,但是它并没有跨它的整个文化传统,所以要必须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界限,不能只是英语中心主义的产物,而应重视用其他语言发表的文学理论著述的作用和经验,并且及时地将其合理的因素融入建构中的世界诗学体系。也就是说,它只要是合理的,我们就应该把它推广,把它用作一种阐释文学现象的理论的模式。我曾经也跟我们有些从事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讲,我说你们假如说要用中国文学理论的视角,《文心雕龙》的建构视角,能够阐释一部西方文学作品,要保证你这个作品翻译成英文,西方学者很愿意读。因为你至少有你的新意,你的新的视角。
第三,世界诗学必须是一种普适性的文学阐释理论,它应能够用于解释所有的世界文学现象,而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古代的还是现当代的文学现象。西方的文论为什么在中国大行其道?就因为它能够被中国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用来阐释中国的文学现象,所以它就具有了某种意义上的普适性。
第四,世界诗学应同时考虑普适性和相对性的结合。就是说应对取自民族/国别的文学和理论批评经验的所有理论要开放,尤其是应该关注来自小民族的但是确实具有一些普适性意义的文学和理论。比如说像鲁文·楚尔的认知诗学,尽管他本人是来自小民族,但是他的理论能够解释其他国家的文学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和跨文化性。
第五,世界诗学作为一种理论模式,在运用于文学阐述时绝不可对文学文本或文学现象进行“强制性阐释”,而应该聚焦于具体的文学批评和理论阐释实践,并且及时地对自身的理论模式进行修正和完善。我们在运用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学现象(时)的情况往往有两种倾向:一种倾向就是用西方的某个理论来阐释一个中国文学作品,最后证明这个西方理论是正确的。我们经常在写论文的时候,甚至写硕士论文、博士论文(时)都是有这种倾向,我经常跟我学生讲,我说你为什么不能跟他进行讨论?他说我哪有这个水平,讨论不了,我只能用他的理论。我说,你用他的理论就一定能够解释中国的文学现象吗?他说有时候也发现不太对头,我说不对头的地方就是你有可能创新的地方,这个时候你要提出你的批判性的见解,然后讨论,然后对他的理论进行重新建构,这就是你的新东西,对不对?拉康对弗洛伊德的理论重新阐述,他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就缺少一个语言的中介,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是没有规律可循的,像一个chaotic,深井一样的。拉康认为无意识也像语言一样是有结构的,这就是拉康的创建。所以哪怕有一点创建,这也是你的真正的一个创建。
第六,世界诗学应该是一种开放的理论话语,应能与人文学科的其他分支学科领域进行对话,并对人文学科理论话语的建构作出自己的贡献。所以我想,因为文学理论家他如果能够提出他的理论建构,被其他学科所用,这也是他的理论具有的跨学科的意义。
第七,世界诗学应该具有可译性。为什么?它不能仅仅是某一个语言当中特有的产物,如果不可译,那就说明它不具有普适意义,它不能够用于阐释其他的文学现象。为什么西方文论在中国可以大行其道,也是因为它能够被汉译,能够被译成中国式的语言,并且被中国化。我们经常提出西方文论中国化,也有人提出汉译西方文论,就认为西方文论经过汉语的翻译之后,它有了一种新的生机。有很多词汇,中国文论当中,古典文论是没有的,经过翻译以后,中国文论就产生了这些术语和概念,所以最后本身也使得西方文论发生了变形。所以,世界诗学应当便于或者能够对英语世界以外的文学作品和文本进行有效的阐述,同时在被翻译的过程中它自身也有所(收)获。所以美国的世界文学理论家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他讲世界文学应该Gain in Translation,就是世界文学应该是在翻译中有所(收)获的。如果你翻译出去之后反而这部作品没有任何意义了,没有人读了,那就说明它不是世界文学。
第八,就任何一种阐释理论,它只要能够用于世界文学作品的阐释和批评,就可以跻身世界诗学,因此世界诗学也如同世界文学概念一样,永远处于一个未完成的状态。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我们从歌德1832年(1827年——编者注)和艾克曼讨论世界文学算起,现在已经是180多年了。实际上在歌德之前,哲学家赫尔德和诗人魏兰也使用过世界文学这样的一个术语,但是他们没有像歌德那样系统地对它进行阐释。所以世界文学的概念时而成为一门显学,时而又被埋没,当民族主义高涨的时候,世界文学就被边缘化,当全球化时代到来的时候,世界文学又成了一门显学,所以我想它应该永远处于一个未完成的状态。
第九,世界诗学既然是可以建构的,那它也应该处于一种不断被重构的动态模式。每一代文学理论家都可以从自己的批评和阐述实践中对它进行质疑、修正,甚至重构。我想,一种理论概念的提出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一定要能够引起别人的重视、讨论,甚至批判,甚至重构,甚至反拨。
总之,世界诗学构想的提出有助于世界文学理论概念的进一步完善,它可以作为一个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值得讨论甚至争论的理论话题,引发国际性的理论讨论,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和修正现有的世界文学和文论的版图。所以有很多人问我,你提出世界诗学的概念,能够在国际上产生反响吗?我说假如说你不去推广,那可能很快就会被埋没了。所以我用英文先发表,中文再发表,然后我的学生把它翻译成意大利文,翻译成法文,翻译成德文,还要翻译成俄文和日文。能够占据这几种语言,我想,一个理论概念逐渐也就成为相对来说具有普适意义了。
在当前的世界文学研究领域,尽管许多学者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关于“世界文学”概念的讨论,但却很少有人去深入探讨与世界文学相关的理论问题。这些学者也不企望建构这样一种世界诗学。而另一方面,世界文学伴随着世界主义这个大的论题的再度出现,已经变得越来越吸引东西方的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者。一些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学者也提出了关于这一颇有争议的概念和一些各种定义。比如我刚才提到的大卫·达姆罗什,佛克马,还有西奥·德汉(Theo D'Haen)等人,他们都提出了他们关于世界文学的建构。当然,我本人也提出了关于世界文学的建构。美国的意大利裔学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朗哥·莫莱蒂,他写了一篇文章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世界文学构想》,是2000年发表在《新左派评论》当中,他就是提出了他的关于世界文学的构想。他其中有一个核心的观念就是说,一个人不可能阅读所有的文学作品的原著,他可以通过一种有距离的阅读,阅读其他人对他的作品的讨论,来了解世界文学。还有David Damrosch(大卫·达姆罗什),他提出了世界文学不应当是民族文学的简略的折射,世界文学必须是翻译中有所(收)获的,世界文学它应该是一种文学生产和流通的翻译的过程,不是一套固定的经典。所以针对他的三重定义,我也在另外一篇英文文章当中就提出了我的三重的定义了。因为Damrosch是反经典化的,我提出世界文学还是应该保留它的经典化,但是要和可读性相结合。Theo D'Haen写了一部简明世界文学的发展史。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和David Damrosch进行大讨论时,就提了一个Global English(es)和Global Chinese(s)的问题。我说中文也是一种复数的中文。
同样,不少学者已经试图将世界文学研究与文学经典的形成与重构以及重写文学史等论题相结合,以便取得一些突破性的进展。但是在我看来,迄今所取得的成果还远远不能令人满意,其原因在于至今尚无人提出自己的全新的理论建构。对文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也依然停留在比较诗学的层面,并没有在孟而康的比较诗学研究基础上作出理论上的升华和建构。因此在提出我的理论建构之前,简略地回顾一下孟而康的比较诗学概念仍有必要。
我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当中就提出,孟而康已经具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建构性的世界诗学的意识,但他没有提出这个概念。确实,孟而康在将东西方的文学和理论著作进行比较研究时,从东西方文学和理论著作中收集了大量的例证,从而发现了“一种生成性的诗学”(Generative poetics)。我认为它是具有一种普适性的。虽然他没有使用诸如“世界”(world)或“普世”(universal)的这类词,但他实际上意在突破西方中心主义或者所谓的“东”“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而建立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诗学体系。因为在他看来,这样一种普遍的或系统性的诗学首先应当是“自满自足的”(他用了systematic、generative、autonomous这些术语),然后才有可能成为具有普适意义和价值的诗学。显然孟而康仍然持有一种充满精英意识的比较文学研究者的立场,集中讨论一些在文学史上已有定评的经典文学,但却很少讨论当代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他的讨论到19世纪文学为止,对20世纪以来的文学基本不讨论。然后他的讨论主要是以西方文学为主,偶尔也涉及一点东方文学,因为孟而康本人是一个日本学研究者,他举例子基本上举的东方就是日本,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他一个很大的局限。他在整个书当中就提到过一次《文心雕龙》,但是也没有展开谈,至少就说明他对《文心雕龙》并没有做深入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孟而康由于英年早逝而未能继续他已经开始萌发的世界诗学的建构,我想这无疑是他的比较诗学的一个局限。
他的另一个局限就在于,作为一位有着精英意识的日本学研究者,他头脑里考虑最多的是日本的古典文学和文论。虽然他在书中也稍带提及了中国的文学理论著作,但却全然不提现代文论,因此他的研究更具有史的价值而并不能引发当下的理论讨论。就作为一部学术著作而言,他的比较诗学确实是很有价值的,包括他的资料的详实性和论述的细致性。
有鉴于此,我认为古代文论基本上是自满自足的和相对封闭的,它要想在今天仍然发挥其应有的阐释作用,那就应当被今天的文学实践激活,通过它的现代转型来实现它的当代功能。假如说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理论在当今不再被人们讨论,不被人们引用,不被人们用来阐释新的文学现象,我想他的诗学理论很快就过时了。它为什么今天还被人讨论呢?因为它在当下仍然被激活了,比如说被孟而康所激活,他提出比较诗学的概念,就从亚里士多德《诗学》开始,我们今天提世界诗学又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所以亚里士多德永远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么一个理论源泉。但是很多和亚里士多德同时代的或者比他后代的一些人就渐渐地在我们的文化记忆当中就被淘汰了。所以我经常跟人家讲,我说世界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文化记忆,也就是说,在你的记忆当中,你读过的作品你还能记住多少部,对不对?这些也许是你头脑里的世界文学的这么一个书目。
我想在此提出这一构想,以便在今后的著述中逐步加以拓展和完善。首先我想强调的是,提出世界诗学或者世界文论这些话题究竟意味着什么?它的目的就在于建构一种有着共同美学原则和普适标准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也许人们会问,既然世界各民族或者国别的文学和文化千姿百态,能有一个普世公认的审美标准吗?我的回答既是否定的,同时又是肯定的:在绝对的意义上说是不可能的,但是依循一种相对普适的审美标准还是可以做到的。就好比说文学评奖,有没有绝对的标准?我说这是没有的,但是可以说在相对意义上还是有的。比如说评委坐在一起阅读一部作品,大家都认为这部作品非常好,那就使得大家的头脑当中就有一个标准,对不对?如果大家都认为这部作品不好,那说明在大家的头脑里的标准,它不符合我们的期待值。因此这样一种世界诗学或者文论就不能是简单地来自西方文学,也不能主要地是来自东方文学,更不能是东西方文学和文论的简单的相加,而应该是一种东西方文论当中的精品、对优秀的作品的提炼和升华。
19世纪后半叶以降的现代文论无疑是开放和包容的。虽然它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欧洲中心主义或者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但它已经被文学批评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当然它同时也是很不完备的。在当今这个跨文化的语境下,它很难显示出其普适意义和价值,因此建构一种具有相对普适意义的世界诗学就是势在必行的。
那么它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世界诗学应该是一种全新的文学阐释理论,应该是经过东西方文学批评和阐释的实践考验,切实可行的理论概念的提炼和抽象,应该在对优秀的世界文学和理论扎实研究之基础上加以建构,这样它才能被用于解释所有的东西方文学现象。这也许正是我们应该超越前人未竟的事业所应做的工作。
我的理由是什么呢?我现在对刚才的九个方面一一阐释。
首先世界诗学必须要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包容产生自全世界主要语言文化土壤的文学理论,因此对它的表达就应该同时是作为整体的世界诗学体系和作为具体的文学阐释理论。既然世界诗学意指全世界的文学理论,那么它就应该像世界文学那样,同时以单数和复数的形式加以表达。由于“诗学”(poetics)这一术语在英文中无法区分单复数,我这里便用“文学理论”来加以表述:作为总体的世界文论(world literary theory)是它的单数,和具体的世界(各民族/国别的)文论叫(world literary theories)。前者指这样一种总体的世界文论所具有的普适意义和很高的标准,亦即它应该是世界优秀的文学理论的升华和结晶,后者则应该考虑到来自不同的民族/国别文学的具体文论和范畴。就前者它是具有普适性,后者它是具有一定的相对性。
但是那些能够被视为世界诗学的理论必定要符合普适性的高标准,必须可以用于解释世界各民族文学中出现的所有现象。因此,仅仅基于某个民族/国别的文学和文论经验而建构的理论,如果不能在另一个民族/国别的文学研究中得到应用或推广,就算不上世界性的诗学或者理论。
其次,世界诗学必须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界限,不能只是“英语中心主义”的产物,而应该重视用其他语言撰写并发表的文学理论著作的作用和经验,并且及时地将其中的合理因素融入建构中的世界诗学体系。这样,世界诗学便具有跨越语言和文化之界限的特征。我们都知道,在西方文化传统中由亚里士多德提出、后来的历代理论家发展完善起来的诗学理论经历了不断的重构,它在用于东方文学作品和现象的阐释时也被东方化,进而也具有了更多的普适意义和价值。而相比之下,在英语世界出版的几乎所有讨论文学理论史的主要著作中,非西方国家的文学理论或者受到全然忽视,或者仅仅被简单地稍加提及,在一部文论史上根本没有占有应有的篇幅和地位。我们都知道2010年美国的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诺顿批评与理论选集》第二版出版,第一次收录了美籍中国理论家李泽厚的《美学四讲》,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了,但是我们看看,美国收录多少呢?美国收录的理论家几乎跟法国相同,美国的文学才有多长的历史呢,200多年,对不对?而且,李泽厚是1930年出生的,美国的批评家已经收录到1960年出生的迈克尔·哈特,在杜克大学担任教授、写《帝国》那本书的理论家,我们中国才只收了一个李泽厚,所以可想而知,中国的文学理论在世界文论的版图上面占有多么微不足道的地位!
课程简介
本课由清华大学的王宁教授主讲,主要谈及比较诗学、认知诗学和世界诗学三个话题。
王教授认为,中国的文学理论也曾对西方学者的比较诗学理论构建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和启迪,对于这一点,绝大多数主流的西方文学理论家却全然不知,在这方面,美国学者刘若愚、法国学者艾田浦、荷兰学者弗克马以及美国学者孟而康等人都做过一些初步的尝试。
王教授在提出世界诗学构想时,除了谈到比较诗学和世界文学,还提及了认知诗学,认知诗学对文本语言因素的关注和奠基人鲁文·楚尔的双重边缘身份等,对他的理论建构都有所启示。
王教授力图建构的世界诗学的特征表现为:必须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必须跨越语言和文化界限,必须是一种普适性的文学阐释理论,应同时考虑普世性和相对性的结合,不能进行“强制性阐释”,应该是一种开放的理论话语,应该具有可译性,永远处于一个未完成的状态,应该处于不断地被重构的动态模式。
此外,王教授还对提出世界诗学构想的理论依据进行了阐述。
王教授认为世界诗学构想的提出有助于世界文学理论概念的进一步完善,它可以作为一个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值得讨论甚至争论的理论话题引发国际性的理论讨论,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和修正现有的世界文学和文论的版图。
(视频拍摄于2015年)
- 为什么将比较诗学、认知诗学与世界诗学放在一起讨论?
- 西方学者的比较诗学理论里的中国元素
- “后理论时代”的提出
- 在当今时代谈论比较诗学是否有点不合时宜?
- 什么是比较诗学?
- 什么是认知诗学?它有什么研究特点?
- 认知诗学的奠基人是谁?
- 认知诗学包含什么?
- 王宁教授在提出世界诗学构想时,提及认知诗学的原因是什么?
- 建构世界诗学有哪些路径?
- 世界诗学构想的提出有什么影响?
- 孟而康的比较诗学概念有哪些局限?
- 提出世界诗学或者世界文论这些话题究竟意味着什么?
- 世界诗学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
- 世界诗学为什么必须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性?
- 世界诗学为什么必须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界限?
- 世界诗学为什么必须是普适性的文学阐述理论?
- 世界诗学为什么要考虑普适性和相对性的结合?
- 世界诗学为什么不能进行“强制性阐释”?
- 世界诗学为什么应该是一种开放的理论话语?
- 世界诗学为什么应该具有可译性?
- 为什么说世界诗学永远处于未完成的状态?
- 为什么说世界诗学处于不断地被重构的动态模式?
- 王宁教授提出世界诗学的构想有哪些理论依据?
- 现如今建构世界诗学是否遥不可及?
- 中国学者在国际文学理论争鸣中应该怎么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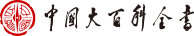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8139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813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