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诗学、认知诗学与世界诗学(三)
尽管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自满自足的诗学体系,其标志性成果就是刘勰的《文心雕龙》,我们也给他推荐了,但为什么不收录?他说我们有亚里士多德《诗学》,所以《文心雕龙》就算了,在当下也没有人使用,我们就把它带过去了,一下子就直接跳到李泽厚。我想后来再收录的人肯定比李泽厚更年轻。但迄今为止,西方的主要理论家几乎对此都全然不知。而在中国,从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学者,如果不知道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贺拉斯的《诗艺》,至少是不能登上大学讲台讲授文学理论课的。但是在西方,不知道《文心雕龙》,不知道鲁迅,不知道钱锺书,不知道茅盾、巴金的大有人在,而且他们不觉得这是一个耻辱,他说,他们的作品有好的英文译本吗?他会反过来问你这样的问题。因此,对中国以及东方诗学的忽略和不屑一顾显然是探讨世界文论或诗学过程中的一个严重的缺陷。作为一位中国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者,我要说的是,编撰一部完整的世界文论史或诗学史,应该包括符合这一标准的主要非西方文论的著作,尤其是像《文心雕龙》这样一部博大精深的文论著作。
第三,世界诗学既然被认为是一种普适性的文学阐述理论,那么它就应能用于解释所有的世界文学现象,而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古代的还是现当代的文学现象。实际上长期以来,东方文化和文学对来自西方的理论一直是持一种包容和拿来的态度。自从近现代以来,中国、日本和印度的比较文学学者早就自觉地开始用西方文学理论来解释自己的国别文学和理论现象。他们在用以解释自己的文学现象的过程中,通过创造性的转化,使得原来仅仅有着民族和地域局限的西方理论具有了“全球的”特征和普适的意义。而在许多情况下,则在与当地的文学实践的碰撞和对话过程中打下了“全球本土”的特征,就是global in the local。但在那些西方国家,即使在汉学家中,文学研究者仍然一直在沿用从西方的文学经验或文化传统中得出的理论来解释非西方的文学现象。例如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这种现象就显而易见。我讲这是在海外的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文学现象是天经地义的。既然我们要建构一种世界性的诗学理论,我们就应该努力克服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否则,一部世界诗学史就会变成西方诗学的简单的扩展版。就像我们刚提到的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你说你有西方中心主义,我说好,我收录了一个李泽厚的作品,这是中国的,对不对?但是他在里面就占一个微不足道的地位,做一个点缀。
第四,世界诗学应同时考虑普适性和相对性的结合,即它应当向取自民族/国别文学和理论批评经验的所有理论开放,尤其应该关注来自小民族,但确实具有普适性的文学和理论。正如美国文论家希利斯·米勒在描绘文学作品的特征时所指出的,“它们彼此是不对称的,每一个现象都独具特色,千姿百态,各相迥异”。米勒写了一本书叫On Literature,一本小说。米勒曾经在清华大学做的演讲当中最后这样结束他的演讲,他说“If I were twenty years younger,I would like to start from studying Chinese”,他要从学习中文开始来掌握世界文学,他觉得读英文翻译是不能满足的。
在各民族/国别文学之间,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泾渭分明的状况,因为每一个民族/国家的优秀文学作品都是具有独创性的,“人们甚至可以把它们视为众多莱布尼兹式的没有窗户的单子,或视为众多莱布尼兹式的‘不可能’的世界,也即在逻辑上不可能共存于一个空间里的众多个世界”。米勒大学本科是学物理学的,后来改学文学,所以他对物理学的这些原则经常也把它应用到文学研究当中。既然诗学就是探讨文学现象,当然也包括文学作品的理论,那么它就应当像那些作品那样内涵丰富和对理论阐释开放。确实,由于某种历史的原因,西方诗学总是比其他文化传统的诗学要强势得多,因此它经常充当着某种具有公认的合法性的标准。而相比之下,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美学原则则很少有可能去影响它,更遑论用以解释来自西方文学传统的现象了。所以我想这一点就是李泽厚的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收入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我想也不会有很多的西方文学家应用他的理论去解释西方文学现象的。这就是目前中国文学和诗学在国际上的边缘化的状态。
孟而康作为一位跨文化比较诗学理论家,始终对西方世界以外的文学和诗学抱有一种包容的态度。他曾经指出,“认为最伟大的文学都是最公正的社会的产物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尽管可以断定,用那一时代的标准来衡量,不公正的社会不可能创造出有持久影响力的作品”。因为过去西方人经常讲,专制的社会是产生不了优秀的文学的,但是拉丁美洲的爆炸文学产生之后使他们的论断被打破了。拉丁美洲的国家是十分专制的国家,它照样产生出像马尔克斯、博尔赫斯这样世界文学大师。世界上不同地区的诗学的情况也大致相同,有时,重要的作家或理论家也许来自小民族或者弱势国家,因此有必要采取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来看待世界上的不同的诗学之价值,却不可重蹈西方中心主义的覆辙。
第五,世界诗学作为一种理论模式,在运用于文学阐释时绝不可对文学文本或者文学现象进行“强制性的阐释”,而应该更加聚焦于具体的文学批评和理论阐释实践,并且及时地对自身的理论模式进行修正和完善。我们不能说我提出的理论就一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用于阐释任何文学现象都有效,有的时候你要做出调整和修正。所谓强制阐释,正如有的学者已经指出了的,就是不顾文学自身的规律,从文学以外的理论视角进入文学,将根据非文学经验抽象出的理论强行用于文学作品及文学现象的阐释,其目的并非为了丰富和完善文学作品的意义,而更是为了通过对文学现象的阐释来证明自己的理论的正确和有效性。所以就以理论先行,最后的结论也是理论,文学现象只不过是作为我的材料而已,这是很多理论家的这么一个做法。
当然,在当今这个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大势所趋的情势下,文学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非文学理论话语的侵蚀。因此在文学研究界,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返回审美”的呼声。从非文学的理论视角进入文学作品并对之阐释本身并无可厚非,但是其最终的目的应该是有利于文学意义的建构和文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所以你可以借助于别的理论来阐释文学,但最后结论应该落在文学上。
第六,世界诗学应该是一种开放的理论话语,它应该能够与人文学科的其他分支学科的领域进行对话,并对人文科学理论话语的建构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与上面一点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里,文学本身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过去在文学的高雅殿堂里没有地位的文类,今天已经堂而皇之地跻身文学之中,这一切均对我们的文学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样,文学理论今天再也不像以往那样纯洁或者自足了。对于这一现象,美国的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称之为“文化诗学”。他试图在经典文学艺术与通俗文学艺术之间进行一种协商和谈判,以便建立一种可以沟通艺术与社会的文化诗学。他也是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现任的总主编。我们再看结构主义文论家是怎么提出来的,结构主义文论家茨维坦·托多罗夫在经过仔细考察文学的变化后也得出这样的印象:“文学的领地对我来说简直大大地拓宽了,因为它现在除了诗歌、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戏剧作品外,还包括了大量为公众或个人所享用的叙事、散文和随想作品。”后者在过去是不登文学的大雅之堂的。确实,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文学本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至于那些毕生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也开始担心印刷的文学作品是否会被新媒体所取代,连米勒这样的文学理论家都有这样的担心。作为文学研究者,我们应该认识到,经典的理论正是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但这不意味着要排除所有那些非经典的理论教义,因为它们中的一些或许会在未来跻身经典的行列。这样看来,世界诗学就不是一个封闭的经典文论的体系,而应当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应当吸纳可用于解释文学现象的所有的理论。有些理论尽管是来自小民族的,有些理论尽管现在还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但是它可以在应用的过程当中逐渐完善和修正。
第七,世界诗学应该具有可译性,以便能够对西方世界以外的文学作品和文本进行有效的阐释。同时在被翻译的过程中它自身也应有所收获。因为世界诗学的一些理论范畴必须经过翻译的中介才能够在各种语言和文学阐释中流通,不可译的理论范畴是无法成为世界诗学的。毫无疑问,翻译会导致变异。有人说“翻译是背叛”嘛。尤其是文学理论的翻译更是如此。理论的旅行有可能使原来的理论在另一语境中失去一些东西,但同时也会带来一些新的东西。理论的翻译有时候失去一些东西,但是它被翻译的过程当中也是一种再创造和建构的过程。因此翻译既是不可能的,同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德里达就说翻译是不可能的,但是也是必须的,Translation is impossible but inevitable。众所周知,一个人不可能通过所有的语言来学习文学理论,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还得依赖翻译,因此翻译就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一种理论通过翻译能够把新的东西带入到另一文化语境中,例如就像西方文学理论影响了中国现代文论那样,那么这一理论就肯定被视为一种世界性的文论或者诗学。亚里士多德的许多悲剧的范畴,一些理论的范畴,都被中国文论家所采用,用于解释中国的文学现象。但是这些中国文论家几乎都不懂希腊语,而且亚里士多德很多著作开始并不是从希腊语翻译过来,而是通过英语,通过其他语言翻译过来的,就可想而知,通过翻译几乎也产生了一种重新建构。同样,如果一种理论、诗学仅仅适用于一种文化语境,那么这种理论就绝不可能被视为世界文论或者诗学。
第八,任何一种阐述理论,只要能够用于世界文学作品的阐释和批评,就可跻身世界诗学。因此世界诗学也如同世界文学概念一样,永远处于一个未完成的状态。各民族/国别的文学和理论批评经验都可以向这一开放的体系提供自己的理论资源,从而使之不断地丰富和完善,最终使之作为一个文学理论范畴而载入未来的文学和理论史。
第九,世界诗学既然是可以建构的,那么它也应该处于一种不断地被重构的动态模式。每一代文学理论家都可以在实际运用时对它进行质疑、修正甚至重构。如上所述,我提出世界诗学这一概念并非旨在提出一种恒定不变的世界诗学原则,而只是想提出一种理论构想,通过这种构想的提出,引发围绕这一构想的理论讨论和争鸣。既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西方理论家建构了现代主义和接受美学,西方的东方学者也根据自己那一鳞半爪的东方文化知识建构各种“东方主义”,我们作为东方的文学研究者,为什么不能从自己的文学经验出发,也综合东西方各国的文学经验,建构一种具有相对普适意义和价值的世界诗学呢?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要提出世界诗学构想的这么一个初衷。西方人建构了很多关于东方的种种概念和国家的形象,中国的形象,比如说认为中国是一个东亚病夫。我今年组织了一个专辑,在欧洲科学院的院刊European Review(《欧洲评论》)发表,题目叫Rediscovering China: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重新发现中国:跨学科的视角》),我邀请了十多位来自不同学科的东西方的学者,对中国进行重新发现和重新想象。有来自社会学的,有来自哲学的,有来自文学的,也有来自语言学的,我也邀请到南京大学的一位学者叫程爱民,也写了一个中国对外汉语的教学。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Promoting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world。当年歌德对世界文学理念的构想在过去的一百八十多年里不断地引发讨论和争论,同时也沉寂了多年,最终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再度兴起,不断地吸引人们对之进行质疑和重构。事实证明,它是一个开放的理论概念,同样,世界诗学的构想也应该如此。
以上就是我力图建构的一种世界诗学之内涵和特征。当然,别的学者也可以提出另一些标准来判断一种诗学是否算得上是国际性或世界性的。但是,上述九条标准应该足以涵盖这样一种建构中的或者构想中的世界诗学的特征。
提出就是世界诗学构想的理论依据。也许人们会问,在当今的西方文论界,建构“宏大叙事”式的理论话语体系早已成为历史,甚至带有许多非文学因素的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也已经成为过去,建构世界诗学有可能吗?或者说,即使建构出一种世界诗学,又能行之有效吗?我想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即“我所提出的世界诗学的构想究竟有何理论依据”?我想,如果没有理论依据我就不会提出了。质言之,这一理论依据主要在于这三个方面,我下面逐一阐述。
第一,世界诗学是基于世界文学和比较诗学研究成果之上的一种理论升华。它并非是理论家躲在象牙塔里发出的无病呻吟,而是根据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实践需要而提出的。它有着丰厚的世界优秀文学作品作为基础,先有了世界文学,先有了比较诗学,然后我才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世界诗学的构想。而迄今占据世界文论主流的西方文论并未涵盖全世界文学和理论的经验,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其自身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经验中抽象升华出来的。尽管这些西方文论往往在用于阐释的时候总是标榜自己是具有普适意义的,是universal,global,但是实际上,它们仍然是带有它们自己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特征。因此用于解释西方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自然是行之有效的,而且经过千百年历史的考验,已经被证明是一种相对普适意义的真理。但是自歌德对世界文学作了“非西方中心主义”的建构后,越来越多的西方理论家开始把目光转向西方世界以外的文学创作经验,他们也出版了自己的世界文学史,对世界文学领域长期占主导地位的西方中心主义形成了有力的挑战。
我们都知道,世界文学史,我刚才举的两个例子。一个是法国学者写的世界文学史,其中中国文学是法国文学的1/12。还有一个是德国世界文学的理论家写的世界文学,压根就不提中国文学,好像世界文学就不包括中国一样。最为可悲的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学者把世界文学这门学科,把它叫做外国文学,这也是中国的一个特色。在国外像美国人谈世界文学肯定是包括美国文学的。我邀请的David Damrosch 2008年到北京语言大学来讲学,参加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八届年会,他提交的题目就是American literature as the world literature。我当时一想,作为世界文学的美国文学,我说这个美国学者勃勃野心。后来也是非常巧了,两个月之后我到美国哈佛大学,我做的题目就是Chinese literature as the world literature,我开始讲了,Inspited by my friend David Damrosch,I delivered this speech,entitled Chinese literature as the world literature.Why? Because the concept would lead hard do,was put forward under the inspiration of Goethe's reading of Chinese literature.最后我也提到了,我说当西方欧洲处于中世纪的时候,中国的许多文学大家早已经蜚声文坛了,包括屈原,包括李白、杜甫,那时美国还没有建国呢!美国人哈哈大笑起来。众所周知,理论概念的提出必须有丰厚的实践基础,既然世界文学的实践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作为文学理论工作者,我们理应提出自己的理论原则,以便对这些异彩纷呈、错综复杂的文学现象加以理论的总结,同时也建构自己的元批评理论话语。因此在这个时候提出世界诗学的构想就是非常及时的。
第二,迄今所有具有相对普适性的文学阐述理论都产生于西方语境,由于其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局限,这些理论提出者不可能将其涵盖东西方文学和理论的范畴和经验。尽管一些重要的理论家凭着自己的深厚学养和理论把握能力,通过强制性的阐释使自己的理论也能够用于非西方文学的阐释,但毕竟漏洞很多。比如说弗洛伊德的理论,我们也可以阐释中国文学现象,我自己过去也做过的,但是后来我发现不对头了,我就对弗洛伊德理论本身进行改造,进行重新建构,通过中国的文学现象对他的理论进行质疑。德里达的理论也可以用于解释中国文学现象,但是我们不能够盲目地运用,必须创造性地能动地批判性地运用。所以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从来自西方的一些理论概念用于阐释中国文学现象时的成败得失中见出端倪。
有鉴于此,一些具有国际视野和比较眼光的中国文学理论家便在长期的实践中,首先创造性地将这些具有相对普适意义的理论原则用于阐释中国的文学现象,并在阐释的过程中对之加以改造甚至重构,因而便在中国的语境下出现了“西方文论中国化”的现象。比如我们老一辈的学者朱光潜先生、王国维先生,就是把西方文论用于中国文学现象的阐释,最后对西方文论使它们中国化。王国维用叔本华的理论来阐释《红楼梦》。朱光潜用西方尼采的悲剧理论,最后得出结论说中国古代是没有悲剧的,对不对?这一现象的出现也为我们提出自己的理论概念和批评话语奠定了基础。
第三,中国学者始终关注西方文学理论的前沿课题,并且及时地将其译介到中国。同时我们又有丰富的东方本土文学和理论批评经验和理论素养。因此在当今这个“后理论时代”,当文学和文化理论在西方处于衰落状态时,我们中国学者和理论工作者完全有能力从边缘步入中心,并在与西方乃至国际同行的对话中提出我们自己的理论构想。我们都知道,当年歌德在阅读了一些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作品后浮想联翩,提出了自己的“世界文学”构想,他说:“民族文学现在算不了什么,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现在每一个人都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使它早日来临。”所以我也把歌德这一段话借用到我这里来。比较诗学现在已经算不了什么了,世界诗学的时代即将到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它早日的来临做出自己的贡献。
但在当时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理念时仍然带有一些欧洲的或德意志中心主义的色彩。他对一些到访的美国青年学者说,你们到德国来就等于来到了世界文学的中心,你们学好了德意志文化和文学就等于学好了世界文学。所以他也有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这么一种色彩。他所呼唤的“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只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而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正如米勒所言,“新的世界文学学科则恰恰相反,因为它可以被看作是为挽救文学研究所作出的最后的一搏。它含蓄地声称,研究全世界的文学是理解全球化的一种方式。”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研究世界文论或建构世界诗学,也是对世界文学创作和经验的理论总结和升华。
总之,如果说歌德当年呼唤世界文学的来临确实有点不合时宜的话,那么在今天世界文学已经成为一种现实的情况下,世界诗学的建构就不会是遥不可及的。作为中国的文学理论家和研究者,我们不仅应当继续在国际文学理论争鸣中发出中国的声音,同时更要在与西方和国际同行平等对话的过程中提出自己的理论话题,并建构自己的理论话语。正是基于此,我才不无冒昧地提出自己的理论建构。当然,我也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来推广,比如说我最近正在给美国一个刊物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组织一个专辑(Special issue),就是组织中国四个文学理论家,也包括我们南京大学的周宪教授,约他写了一篇文章,都用英文,我们再发给四个欧美的理论家来评论。你们不是不懂中文吗?我们中国人写出英文的文章来,你来评论,促进中西文论家在同一个层次上进行对话,最后在美国的一个顶尖刊物上发表出来。我想这样也就使得我们中国的文学理论就不至于患有失语症了,而是真正在国际上发出强劲的声音。好,谢谢大家。
课程简介
本课由清华大学的王宁教授主讲,主要谈及比较诗学、认知诗学和世界诗学三个话题。
王教授认为,中国的文学理论也曾对西方学者的比较诗学理论构建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和启迪,对于这一点,绝大多数主流的西方文学理论家却全然不知,在这方面,美国学者刘若愚、法国学者艾田浦、荷兰学者弗克马以及美国学者孟而康等人都做过一些初步的尝试。
王教授在提出世界诗学构想时,除了谈到比较诗学和世界文学,还提及了认知诗学,认知诗学对文本语言因素的关注和奠基人鲁文·楚尔的双重边缘身份等,对他的理论建构都有所启示。
王教授力图建构的世界诗学的特征表现为:必须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必须跨越语言和文化界限,必须是一种普适性的文学阐释理论,应同时考虑普世性和相对性的结合,不能进行“强制性阐释”,应该是一种开放的理论话语,应该具有可译性,永远处于一个未完成的状态,应该处于不断地被重构的动态模式。
此外,王教授还对提出世界诗学构想的理论依据进行了阐述。
王教授认为世界诗学构想的提出有助于世界文学理论概念的进一步完善,它可以作为一个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值得讨论甚至争论的理论话题引发国际性的理论讨论,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和修正现有的世界文学和文论的版图。
(视频拍摄于2015年)
- 为什么将比较诗学、认知诗学与世界诗学放在一起讨论?
- 西方学者的比较诗学理论里的中国元素
- “后理论时代”的提出
- 在当今时代谈论比较诗学是否有点不合时宜?
- 什么是比较诗学?
- 什么是认知诗学?它有什么研究特点?
- 认知诗学的奠基人是谁?
- 认知诗学包含什么?
- 王宁教授在提出世界诗学构想时,提及认知诗学的原因是什么?
- 建构世界诗学有哪些路径?
- 世界诗学构想的提出有什么影响?
- 孟而康的比较诗学概念有哪些局限?
- 提出世界诗学或者世界文论这些话题究竟意味着什么?
- 世界诗学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
- 世界诗学为什么必须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性?
- 世界诗学为什么必须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界限?
- 世界诗学为什么必须是普适性的文学阐述理论?
- 世界诗学为什么要考虑普适性和相对性的结合?
- 世界诗学为什么不能进行“强制性阐释”?
- 世界诗学为什么应该是一种开放的理论话语?
- 世界诗学为什么应该具有可译性?
- 为什么说世界诗学永远处于未完成的状态?
- 为什么说世界诗学处于不断地被重构的动态模式?
- 王宁教授提出世界诗学的构想有哪些理论依据?
- 现如今建构世界诗学是否遥不可及?
- 中国学者在国际文学理论争鸣中应该怎么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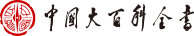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8139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813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