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经典的英译与思想对话(一)
我刚刚走路的时候腿稍微有一点瘸,不是我的腿有残疾,也不是腿碰了,前一段时间医生说是痛风!痛风很多人都有。英文里,痛风是有区别的。有一种叫rich man's gout,富人的痛风,吃得太多了,太好了。还有一种叫poor man's gout,穷人的痛风。我的医生跟我说,your case must be the poor man's gout,他(说)不是吃太多了,是因为吃饭不定时。我从这次得痛风突然有一种想法,我觉得文史哲的同学,包括文史哲的学者,需要不同学科之间的平衡。这也是我为什么拿宗教学的东西给外语学院的同学讲,因为在宗教学研究者来看,很多大家比较熟悉的领域,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这些不同的看法可能对未来的学术研究有一点好处。从根本上讲,宗教学研究就是最根本的comparative studies。从有宗教学开始,西方有一个学者被认为是the father of religious studies,这个人就是英国学者Max Muller。Max Muller建立所谓的religious studies,他的基本名言是他化用歌德的话,he who knows one knows none,只懂一个东西,其实什么都不懂。什么是religious studies?就是讲comparative studies of different religions,而不是一种Christian Origins或者Buddhism studies。这几年,我写了很多这方面的东西。这个题目可长可短,电子文本已经留在桌面上了。里面有些东西可能是需要读的,不是听的。因为有些西方的,特别是跟宗教学、哲学有关的,有很多说法,有时候听不太清楚,要读,要自己去品,去琢磨他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你才可能知道到底在说什么。
第一个举的是德里达的例子。德里达经常是把话绕着说,有很多话令人费解,但就我的经验而言,凡是德里达的东西,看不懂的就去看英文,看英文就懂了,看中文不懂是翻译的问题。德里达法文的东西如果不懂,看英文就会懂,因为英译者基本都是研究德里达的人,所以有时候会有一点解释性的东西,反而比较容易懂。他有一个说法很奇怪,只有他这样的人才能想得出来。他有一个很小的小册子,1980年以后每一个思想界的大师去世以后,跟他有交往的,他都会写一篇祷文。他把这些祷文合起来,出了一本集子,叫做The Work of Mourning。没有中译文,有人把它译成《追思》或《追思集》,仔细读的话,《追思》更好。因为他在里面也是玩文字游戏,说when the mourning works(当那些祈祷起作用的时候),他要干啥,他才说这些,所以他把整个集子叫做the work of mourning。他在里面说一个生命从他得到名字那天起,名字就注定比生命更长久,注定可以“无他而在”。the name begins during his life to get along without him,当你被称为你的时候,你的名字注定是可以无你而在的,所以名字是如此重要。中国古代典籍被翻译成外文时,也意味着中国思想在其他概念系统中rename(被重新命名)。这个名字和原来的生命体之间的关系非常有意思,有没有可能可以get along without him,有没有可能变成另外一种东西,那就是西方文论里经常说的supersign,变成言指,可能跟原来的意指过程已经不太一样。这种“无他而在”怎么才能成为一种存在?如果对比西方经典的话,最有趣的关于名的说法是《圣经》里的“不可妄称上帝之名”,所以才有耶和华,都是不能叫“上帝”的,没有这个名字。中国没有基督教的《圣经》,但是中国的classics被西方人译成经典,编这套丛书的很著名人物就是Max Muller,西方的宗教学之父,他把丛书的名字叫做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东方圣书。传教士翻译的中国经典很多,叫做the sacred books of China,中国的圣书,这些书虽然是classics,但不一定是sacred books,但他们也把它看成是scripture,是一种神圣的经典。这样的圣书如何能为名,就是西方人翻译它的时候,如何给它重新命名,这些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这些年来,经常会听到很多从事西方研究的人对这些翻译进行批评,觉得翻译里可能有很多错误,有很多误解,有很多误读等,特别是西方人的批评,所以才有各种各样的中国古代典籍的重译工程。中国现在启动的这种工程非常之多。为什么要重译,就是因为西方人对中国思想了解得不够,或者说西方人了解的中国思想是被西方概念重新命名了的中国思想,里面已经没有中国自己的声音了,所以我们要重新把它介绍给西方人看,这可能也是有必要的,但是效果到底如何,要看具体的文本才知道。当西方人受这些批评的时候,可以回头看一看,是不是真的如此,比如命名可能会有差异,会把你的生命体放到另一个概念系统当中去,你可能会失去你。
西方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是早期伦敦遣使会派到中国来的,在香港生活了差不多30年,回到英国后被牛津大学聘请为第一位汉学教授(Chinese professor),讲中国语言和文化,(在英国)待了21年。传教士被派到中国最正当的工作是把《圣经》译成中文给中国人看,或者向中国人传教。但理雅各非常有趣,之所以成为我们现在知道的James Legge,不是靠他的传教、布道。他的布道文有很多手稿,现在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图书馆里,很少有人真正对那些东西做研究。他真正留给世人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他几乎把中国的四书五经全部翻译成了英文。他51年(在中国的30年和在英国的这21年)干的基本上都是这件事。理雅各刚到中国来的时候,参加了《圣经》的中译工作,很有名的译本叫做Delegates Version(委办译本),各个偏差会集合起来,共同推出有点权威性的译本。这个译本最有意思的两件事是:第一是把很多重要的概念统一了,比如“道”,“太初有道”,《圣经·约翰福音》里面的第一句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大写的“道”,the Word was with God。the Word was God,“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Word”被译成中文的“道”就是从Delegates Version开始的,它是理雅各亲自参与的。若干年后,理雅各把《道德经》译成英文时,也涉及“道可道,非常道”,但他坚决拒绝把“道”译成任何一个英文词。他说翻译“道”的最好方法就是用它的发音TAO,而不是找任何一个English terminology equivalen……,它没有equivalence(同义词),他觉得找不到。如果传教士在他的基督教背景中,深深地知道不可妄称上帝之名,那么他就非常容易地理解“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个“名”是不能名的,所以“道可道,非常道”,理雅各的译文就the tao that can be trodden(可以被践履,可以被实现),实践的“道”,is not the eternal tao,不是最终的“道”,the name that can be named,可以被命名的“名”is not the eternal name,不是最终的“名”。他对基督教的理解有非常有趣的张力,这可以帮助他更好地理解《道德经》,来讲“道”和“名”。理雅各认为翻译中国概念的最佳方式就是把它挪用到译文当中,不是为它找一个相当的英文概念。
与理雅各相反的是中国人自己的尝试。这位中国人不是一般的译者,是大名鼎鼎的辜鸿铭。辜鸿铭觉得要向西方人传播正宗的中国文化,传播正宗的儒家传统。他对理雅各意见很大。他在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上学,理雅各是苏格兰人,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伦敦遣使会)的根就在苏格兰,所以他跟理雅各有点关联。辜鸿铭在爱丁堡读硕士学位,读书的时候写了一本著名的书,叫《中国(人)的精神》(The Chinese spirits)。他觉得理雅各做得不好,所以要重新把它翻译成英文,引用了歌德等西方作家翻译《论语》之作,来解释《论语》,解释孔子的说法。他觉得要使它在西方的理解系统中让人变得更容易明白,才能被西方人接受。但是这个译本很少被人当成真正的译本,之所以它还有价值,因为它的译者是辜鸿铭,比较特别。《论语》的英文译本至少有300多个。我还有一个很奇特的美国人翻译的版本,他把《论语》的顺序完全打乱,按照《周易》的卦象重新排,左边是《周易》的卦象,右面是《论语》里跟卦象相对应的话。他的整个重新排也有他的理由,他说《周易》是在西方被翻译得最多的一本中国典籍,要让人觉得孔子的说法跟《周易》有关联,才会吸引很多人。但《周易》有多少中国人看得懂都是个问题,虽然它确实译本很多,但是到底怎么把它准确地传达出来,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辜鸿铭认为理雅各的译文不行,觉得自己对中国的传统的理解,先天比理雅各透彻。王国维比较了辜鸿铭和理雅各的译文之后,说:“宁以理雅各氏之译……犹得……真意者也。”他看了辜鸿铭译的《中庸》,觉得好像译得也不错,但说他是翻译中国古代典籍,也不是,他觉得如果这样译还不如理雅各的。
中国的典籍当中,不同的解释非常多,历代就有各种各样的争论。比如孔安国和朱熹对《论语》的注,也有“正解/误解”的辩难,说法从来都是不一样的。顾颉刚说,孔子对中国人来说也会因时而异,因人而异,也是不一样的。杨伯峻,杨树达先生的侄子,专门注中国古代典籍。他在注《论语》时也专门提到,很多古人的注释都是用后代的词义来解释古书。在中国自己的解释系统当中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只是苛责像理雅各这样的人误解、误译、误读,其实大可不必。王国维说,古代经典“无论何人,不能精密译之”。西方人译中文就像后人解释古人的典籍一样,都是重新的命名,就像德里达说的可能会get along without him,是完全有可能的。翻译的问题和解释的问题从来都是关联在一起的。如果看诠释学的书,伽达默尔等人都认为理解已经是一种重新的诠释,何况翻译、解释。西方有诠释学(hermeneutics),诠释学之说来自中世纪的解经,这个词叫exegesis。中国古代传统的注书和中世纪神学家注经很像,把各种各样的解释(interpretation)变成一种解释的科学、解释的学问,就是所谓的hermeneutics。
中国人和西方人谈到翻译,谈到解经的时候,都会引到孟子的“以意逆志”,《孟子·万章上》里的一句话。理雅各在翻译中国经典(Chinese classics)的时候,第一卷四书五经的题记,引的就是《孟子·万章上》中的“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但以谁的意逆古人的志,是以理雅各的意,理雅各助手王韬的意,还是以我们的意,一直都是问题,而且历代的解释大不相同。汉代儒生在解读《诗经》时都强调“以意逆志”,有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之争,争得非常激烈,而且产生了特别多被人看成是穿凿附会的东西。这些歧义导致董仲舒有“《诗》无达诂”的说法,《诗》指《诗经》。《诗》没有“达诂”;“《易》无达占”,《周易》没有确切的解释;“《春秋》无达辞”,《春秋》没有非常精确的历史记载。按董仲舒的说法,《诗》《周易》和《春秋》也许可以代表三种人类的基本精神活动的方式——文学艺术、哲学思辩、历史记忆,这种三种东西“无达诂”“无达占”“无达辞”,是很绝望的一件事。我在看到董仲舒这句话的时候,经常想到英国神学家Thomas Torrance的一句名言,特别像中国的绕口令,it’s impossible to picture how a picture pictures what is pictures。it’s impossible to picture 很难描述,how a picture一个描述,how a picture pictures what is pictures,一个描述是怎样描述它所描述的东西,这是很难描述的。Thomas Torrance曾经在中国四川待过很多年,是个传教士,后来变成很好的神学家。他的儿子也是美国的神学家,现在退休了,到了爱丁堡大学,这些人对中国很有感情。我有时候怀疑他们为什么说这么绕的话,就是他要用一种非常困难的语言方式去表达语言的困难。用这种困难的语言方式说一句话,要仔细想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他觉得语言的困难就在这里。好像我们都说得很清晰,在表达很清晰的思想,其实真的未必,里面会有非常多的歧义。
董仲舒讲“《诗》无达诂”,针对的就是“断章取义”“任意解释”的不好风气,想让它回到大家比较能公认的解释上,但结果是“无达诂”,而且董仲舒的这个说法到宋代以后被普遍化了,“诗无达诂”,诗已经没有书名号,变成普遍的诗,普遍的文学艺术都得不到准确的解释。到清代,中国古代文论专门有说法叫做“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作者本来不这么想,但是我读出这意思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传统从“以意逆志”针对随意解释的积弊,最后变成“《诗》无达诂”,又变成普遍化的文学“无达诂”,最后变成作者可以被读者重新读解,“以意逆志”的初衷可能已经偏移了。这在中国、在西方都是存在的,不是翻译成英文才有,用现代汉语翻译古人、理解古人时也有同样的问题。
王国维试图从《孟子·万章下》里找出一些意思来补充“以意逆志”。
翻译是很难的一件事。王国维先生说,无论何人不能精密译之,中国人、西方人都一样。现在热衷于推出新的译本,不如把已经有的历代译著仔细地梳理一下。这是我这几年一直在推动的事,叫中国古代典籍英译本的汇释、汇校。《论语》至少有300种以上的英译本,《道德经》可能会有200多种英译本,不说其他文字,大量的译本是没有必要看的。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人,像理雅各,不仅有翻译,而且有非常多的注释。西方基督教的《圣经》,历代神学家不断地给它添加注,commentaries of Christian Bible,commentaries的传统,在理雅各译中国经典的时候完全被承袭下来。
课程简介
中国人民大学杨慧林教授在本次讲座中主要讲述了中国古代经典的英译情况及其体现的中西方之间的文化接触和思想对话。
讲座一开始,杨教授以德里达的“无他而在”为例,引出中西方经典关于“名”的一些问题,提出中国经典在被英译的时候,可能也意味着中国的思想在其他概念中被重新命名。接着指出西方人在英译中国经典时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介绍了理雅各、辜鸿铭等人翻译中国经典的一些方法。
随后,杨教授介绍了中西方翻译时存在的“以意逆志”的现象,由此谈到梳理历代译著的重要性,他认为通过解读中国经典英译本,可以从中发现中西方是如何进行文化接触和思想对话的,如西方的“reciprocity”与《论语》中的“恕”的关系;中西方之间的“经文辩读”;儒家金律的英译;“以德报怨”和“以直报怨”的翻译争论等。他还着重介绍了理雅各在翻译中国经典时,将西方经典与中国经典进行关联的做法。
在谈到中西方之间的“经文辩读”时,杨教授主要从跨文化和比较研究的角度加以论述,提出“经文辩读”应该是向所有人敞开的、寻求智慧的活动,没有人能排他性地占有经典的最后意义。
讲座的最后,杨教授再次强调了梳理历代英译本的重要性。
(视频拍摄于2013年)
- 德里达的“无他而在”的解释
- 西方人英译中文存在的问题
- 理雅各翻译中国典籍的方法
- 辜鸿铭翻译中国典籍的方法
- 中国人对自己典籍的解释有哪些?
- 中西方翻译的“以意逆志”有什么差异?
- “《诗》无达诂”与“诗无达诂”的由来
- 为什么说“大道废”才“有仁义”?
- 如何翻译和解读“韬光养晦”?
- 西方reciprocity与儒家“恕”的关系
- 中国思想如何进入西方的概念系统?
- 希腊的神话故事——宙斯吃掉Metis
- 不同宗教的传统溯源
- 如何理解经文辩读方法中的“寻求智慧的活动”?
- 如何理解“相似的至善可以得到不同的显现”?
- 西方“经文辩读”的学者与中国学界有哪些互动?
- 王韬、洪仁玕对理雅各翻译的帮助
- 孔汉思提出的global ethic概念是什么?
- 如何理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金律的否定式表达与肯定式表达有什么区别?
- 理雅各如何翻译“以德报怨”?
- 基督教经典中与“以德报怨”类似的说法有哪些?
- 马丁·路德如何解读宗教戒律?
- 理雅各译经时怎样将《论语》与《圣经》联系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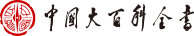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8139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813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