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经典的英译与思想对话(二)
中国经典的排版,大概1/3是原文,1/3是他的译文,1/3是commentaries。除了这些外,还有长篇的导言,有非常详细的注解。这些是现在的人去看西方人究竟怎么理解中国思想非常重要的依据,也是很有意思的再研究资源。所以只是说西方人的译本不好,西方人的译本有错误,没有多大意义,更重要的是认真地梳理他们到底怎么样误解、误译、误读了中国的思想,这种误解、误读、误译中能看到中西思想之间真正的碰撞。这样的工作才能直接进入西方学术对中国文化的真实理解和真实接受。后世可以追究各种区别,比如像理雅各一代人,他们可能跟朱熹这些人解经的方式非常像,目的可能也很像,就是把中国的儒家神圣化。后来也有一些译家比如韦利的译本,他非常明确地主张把儒家去圣化。他不认为孔子是宗教信仰的对象。这两种不同的思路、不同的立场在他们的译文里都会有体现。无论哪一种译文,追究它的话,都可以还原中国和西方思想对话的深刻轨迹。
举个例子,用“圣言”(the Word)关联中国《道德经》所说的“不可道”之“道”;理雅各用“自义”(self-righteousness)解释《道德经》里的“大道废,有仁义”,因为righteousness,我们把它翻译成正义,但是在西方基督教的概念系统当中,说到righteousness时,基本的意思是self-righteousness,自义,自以为正义,不是客观的或者别人认为的。《新约圣经》里,righteousness、justice、justification这些用法只能用被动式,不能是我自己以为我自己是正义的,我自己被我justified,这是不行的,都用被动式。主动的正义,self-righteousness在基督教系统里翻成自义,是相当负面的意思,才可以解释“大道废,有仁义”。
用《道德经》里的“虚用”(use of emptiness),来注说所谓的韬光养晦,就是理雅各为什么解释“韬光养晦”,比现在很多外交官讲的“韬光养晦”好得多。有很长时间里中国人把“韬光养晦”翻译得很可怕,外国人看了真的有点害怕,觉得这人能跟他打交道,能跟他交朋友吗?外交部的高级译员把它译成keep low profile,我觉得翻得很好,给我们自己一个说辞,但不是keep low profile的意思。理雅各可以把“韬光养晦”回到中国的先秦典籍里,找出一套非常好的说法,他不是要为中国文化辩护,而是他认为真正的中国文化的意思,“韬光”不是后世说的“韬光”。
最后一个例子可以跟现代人的说法连起来。去年,欧盟常任理事会主席、原比利时首相范龙佩在会上发表了一篇非常有意思的讲话。会议讨论的是欧盟的战略伙伴关系。欧盟建立了八个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包括美国、俄罗斯、中国,但是欧盟内部有很大争议。建立的Strategic Partnership(战略伙伴关系),八个Partnership,仔细分析里面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在重大问题上跟我们的意见都不一样。费那么多钱,费那么大事,建立Strategic Partnership有什么用?他们开会专门讨论。范龙佩说,在这个战略合作伙伴的框架里(in the frame work of Strategic Partnership)最重要的概念(the most important notion)是reciprocity。reciprocity,网上都把它翻译成互惠互利,肯定是对的,但reciprocity在西方是非常宗教化的一个词,它和神学直接的关联就是correlation(相关呼应)。correlation是神学家才用的词,指的是历史和现实的相关呼应,神学和世俗的相关呼应,上帝和人的相关呼应。这个reciprocity就是相互的关联。所以说它是互惠互利,没问题,但是这个互惠互利更多的可能不是互相得到真正的物质利益,得到好处,而是得到相互的理解。所以再追溯reciprocity,在西方和中国概念系统交接的地方,就是《论语》里面的“恕”,就是“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忠恕而已”的“忠”经常被翻成loyalty;“恕”翻成很多,forgiveness、pardon、mutual tolerance等,但理雅各用的是reciprocity。它和朱熹对“忠”“恕”的解释恰好暗合。朱熹讲“忠”是“尽己之谓忠”,讲“恕”是“推己之为恕”,“恕”就是人之间的一种关联。推己及人,相互理解,就是“恕”。理雅各用reciprocity翻译时,下面就是朱熹的注——推己、尽己,用它们来解释“忠”和“恕”。“恕”很有趣,现代汉语理解是“如心”,将心比心,“如心”。但是如果查古汉语,这个字也是这样写,没有变化。如果查许慎的《说文解字》,就会发现,“如”,“从心如声”,只是一个发声的部分(phonate part),没有任何意思,所以解释成“如心”是不通的。我们有很多中文的语法书,中文的词典,中文的方言,都是从传教士开始做的,这些人用“如心”解释中国的“恕”。如今不是用“如心”解释中国的“恕”,很多对外汉语的教师都是用“如心”来解释中国的“恕”。经过这么一个回合,往前查的话,可以查到《论语》的原文,后来查到朱熹的集注,查到其他人的一种理解,查到理雅各的翻译,最后可以查到范龙佩讲的欧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最核心的概念,也是这个意思,过程非常复杂。我相信范龙佩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可能不知道它的来源居然跟《论语》有关系。
时任国务委员的刘延东到欧盟访问时,跟欧盟理事会签中欧文化交流协议。当时人大送的礼物的盒子上面写了这个reciprocity,写了拉丁文、希腊文等的“恕”,也写了中国的“恕”字,下面有两句话,一句话是范龙佩的,一句话是理雅各的,范龙佩的是说欧盟合作伙伴关系的most important notion,理雅各的是翻译《论语》里的话。送给范龙佩,他非常高兴,他没想到把他跟孔子放一块。这些东西可能让我们看到前人的一种努力,无论这种努力多么微小,但是很不简单,他试图在中国思想和西方的概念系统当中搭建一个通道。
中国思想到底是怎么进入西方的概念系统的呢?西方人用西方的概念系统重新解释中国思想的时候,可能把中国思想淹没了。但是有时候,恰恰是在西方人用西方的概念工具来重新命名中国思想的时候,也把中国思想带到了西方的概念系统当中。理雅各做的很多事情都是这样,这也许不是他的初衷,但他是会变的。西方有个很有名神学家叫卡尔·巴特,他说我们都在说subject、subjectivity(主体),但是真正的subject是moving subject(移动的主体)。诠释学里都讲了很多,fluidity就是流动性。理雅各最有趣的变化,就是翻译中国经典的时候,有时翻一遍,他会修订。就《论语》而言,第一版是1860年,第二版是1893年,第三版时他早就去世了,是别人帮他整理的,1960年出版。1893年和1860年的版本有很多变化,最重要的变化是他前面写的序言。序言里面有一句话,变化之大,看了会让人吃惊,会让人质疑是不是把理雅各的排版排错了。但是他真是有重大的改变,在1860年他写孔子的时候,说,“我越读他的书,越研究孔子,我越觉得他不是一个伟人,他不是一个大的思想家,他的著作可能在中国人那里很快就会销声匿迹。”1893年,30多年以后,这一句话,他稍微做了点调整,改成:“我越读他的书,越研究他,我越觉得他是个伟人。”完全改了,是非常巨大的变化。说他不仅对中国人重要,对传教士也非常重要,非常有帮助。一个人研究一个东西,30年能有这么大的变化,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真实的中国思想才进入真实的西方概念系统,而不是硬搭建一套概念系统塞到西方概念系统,两个东西不对接是没有办法的。
希腊神话里面有一个Metis。Metis可能不太有名,但是她的丈夫很有名,就是主神宙斯。最主要的传说是Metis曾经帮助她的丈夫变成了众神之王。但是有一个神谕说她生出来的孩子会比她的丈夫更强大,会挑战宙斯主神的地位,于是在孩子没出生前,宙斯把Metis吃了。但是Metis被吃了后,换了一种存在方式,她没有消失,小孩最后一定要生出来,就是雅典娜。所以希腊神话里说雅典娜生出来的时候,她父亲头疼得不行,雷神用斧子把头劈开,雅典娜全副武装从头里跳出来。宙斯把Metis吃掉了,好像秩序得以延续,他还是主神,但是Metis被吃了以后,她的存在形式变了,她好像不在了,但是她其实还在,所以她这个名字可以get along without him(可以无她而在),她在宙斯的身体里。最有趣的是不仅雅典娜生出来了,宙斯后来多了一个称号,叫做the One Metis。他把她吃掉了以后,他成了Metis。这个故事是非常有意思的文化隐喻,到底谁吃了谁,宙斯吃了Metis,还是Metis把他变成Metis。这个里面提的问题也许太夸张,是理雅各翻译了《论语》,还是《论语》翻译了理雅各?因为33年之后理雅各居然变成这样一个人。如果再去看他的书,会发现他翻《论语》时,翻译儒家经典时,他对里面有很多质疑,有很多是他不接受的,甚至在译文当中他会说这个东西可能不如基督教等。但是他翻《道德经》的时候,他有非常多的共鸣,有更多的认同。也许《道德经》里有很多东西跟他的基督教神学更有碰撞,更能激发出一些新的想法。也许不是一个结论,但是它可能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考虑。
这些年西方有一群学者参加Scriptural Reasoning(经文辩读)的运动,scripture在西方是很明确的,指的是sacred scriptures(神圣的经典,神圣的文本)。他们刚刚开始做Scriptural Reasoning时,叫text reasoning(文本的辩读),就是关于text一种比较的阅读,或者是text in context,在具体处境中对具体文本的解析。最开始依据的三个主要文本是基督教的《圣经》、犹太教的经典和伊斯兰教的《古兰经》。犹太教的经典后来被基督教称为《旧约》(old testament)。基督教觉得自己的经典成为基督教的历史和犹太教的传统是关联起来的,于是有了《旧约》和《新约》合起来的《圣经》。如果读《古兰经》,会发现《古兰经》里有很多东西跟《圣经》或者说犹太教经典里面记载的东西是相似的,有的是完全一样的,有的是重合的,人们把这三个宗教叫做亚伯拉罕系统(abraham tradition),因为这三种宗教都会追溯到亚伯拉罕。中文的《古兰经》里有一个人叫做易卜拉欣,小的时候读起来觉得像北京牛街一带回民伊斯兰的名字。后来长大了,才知道易卜拉欣是从英文的abraham翻译过来的,就是亚伯拉罕。另外,圣母玛利亚的丈夫是一个木匠,叫约瑟(Joseph),这个名字在《古兰经》里被汉语译成优素福。优素福听上去也觉得是穆斯林,其实就是Joseph。三大宗教系统,都出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所以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当做互文去研究的。于是学者们把这些宗教原来的经典拿到一起做比较阅读,大吃一惊,发现有很多东西原来是那么的相似,甚至是完全一样,但是后来不同的宗教在发展过程当中被不同地解释。不要说三大宗教,基督教就有许多派别,如新教、天主教、东正教,新教里有多少个denominations,数都数不清楚。美国有个宗教史学者,说不要叫Christianity,最好还是称Multi-Christianity(多种多样的基督教),因为没有一个。他说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有25000个教派,而25000个教派在发展过程当中基本上都是打得不可开交,分裂了。所以说基督教的时候,至少面临5万个不同的团体,都是从里面分化出来的,后来有那么大的区别,那么大的冲突。
这些学者把这些不同的宗教传统重新追溯到源头,重新看他们经典的时候,才发现同出一源,有很多东西是非常相似的,于是总结出几个基本看法,说scriptural reasoning是wisdom seeking engagement(寻求智慧的一种活动)。如果是寻求智慧的活动,它应该向所有的人敞开,而不是因为他是基督徒,他才能读基督教圣经。我们在阅读经典的过程当中,才会意识到没有任何人能排他性地独自占有经文的最终意义(nobody exclusively owns the final meaning of the scripture),除了你的读解,可能也会有别人的读解,别人的读解和你的读解也许是同样的合理,同样的有道理,同样可以成立的。他们强调没有任何权威的观点和原本的解释者(authoritative overviews or native speakers),我们现在说的不是中文、英文、希伯来文,我们说的是意义,我们说的是真,要追求的那个真。在这样的问题上,谁都不是说母语的人,因为“真”不是属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群体,一种特定的传统或者一个特定的文化。每一个人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合法地参与进去。没有一个exclusively owns the final meaning of the scripture,而且在寻求真的过程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说自己是native speakers。基督教神学家推出这样的结论,其实是不奇怪的,因为他们早就意识到基督教经典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translatability(可翻译性)。基督教经典是关于耶稣基督的信仰,但是查遍《圣经》,耶稣基督的信仰,用耶稣基督的母语来表达的只有四个地方,而且每个地方都不是一句话,只是一个短语或者一个词,其他的全部都是翻译,全部都不是耶稣的母语,所以说基督教《圣经》本身就是翻译的结果。
课程简介
中国人民大学杨慧林教授在本次讲座中主要讲述了中国古代经典的英译情况及其体现的中西方之间的文化接触和思想对话。
讲座一开始,杨教授以德里达的“无他而在”为例,引出中西方经典关于“名”的一些问题,提出中国经典在被英译的时候,可能也意味着中国的思想在其他概念中被重新命名。接着指出西方人在英译中国经典时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介绍了理雅各、辜鸿铭等人翻译中国经典的一些方法。
随后,杨教授介绍了中西方翻译时存在的“以意逆志”的现象,由此谈到梳理历代译著的重要性,他认为通过解读中国经典英译本,可以从中发现中西方是如何进行文化接触和思想对话的,如西方的“reciprocity”与《论语》中的“恕”的关系;中西方之间的“经文辩读”;儒家金律的英译;“以德报怨”和“以直报怨”的翻译争论等。他还着重介绍了理雅各在翻译中国经典时,将西方经典与中国经典进行关联的做法。
在谈到中西方之间的“经文辩读”时,杨教授主要从跨文化和比较研究的角度加以论述,提出“经文辩读”应该是向所有人敞开的、寻求智慧的活动,没有人能排他性地占有经典的最后意义。
讲座的最后,杨教授再次强调了梳理历代英译本的重要性。
(视频拍摄于2013年)
- 德里达的“无他而在”的解释
- 西方人英译中文存在的问题
- 理雅各翻译中国典籍的方法
- 辜鸿铭翻译中国典籍的方法
- 中国人对自己典籍的解释有哪些?
- 中西方翻译的“以意逆志”有什么差异?
- “《诗》无达诂”与“诗无达诂”的由来
- 为什么说“大道废”才“有仁义”?
- 如何翻译和解读“韬光养晦”?
- 西方reciprocity与儒家“恕”的关系
- 中国思想如何进入西方的概念系统?
- 希腊的神话故事——宙斯吃掉Metis
- 不同宗教的传统溯源
- 如何理解经文辩读方法中的“寻求智慧的活动”?
- 如何理解“相似的至善可以得到不同的显现”?
- 西方“经文辩读”的学者与中国学界有哪些互动?
- 王韬、洪仁玕对理雅各翻译的帮助
- 孔汉思提出的global ethic概念是什么?
- 如何理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金律的否定式表达与肯定式表达有什么区别?
- 理雅各如何翻译“以德报怨”?
- 基督教经典中与“以德报怨”类似的说法有哪些?
- 马丁·路德如何解读宗教戒律?
- 理雅各译经时怎样将《论语》与《圣经》联系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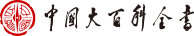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8139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813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