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铁匠”坚守古老行当
茫茫人海中,他们只是普普通通的凡人;
大千世界里,他们从事着简简单单的工作。
然而,因为多一份坚持,多一份坚守,多一份坚韧,
他们看似平凡的人生却谱写出不一样的乐章。
梦想点亮了平凡的人生,行动成就了别样的精彩。
一场大雪过后,阳光从覆盖着雪条的树枝中间透过来。在辽宁新宾镇的刘家村,徐万祥、徐万海哥俩推着手推车从院里走出来,径直走向他们的工作间--铁匠铺。这间用黄泥垒成的土坯房经历了几十年的风吹雨打,沧桑中略显凄凉。炉膛里的炭火生了起来,叮叮铛铛的打铁声传到屋外,仿佛像人们诉说着老哥俩对铁匠这个古老行当的默默坚守。
徐万祥、徐万海哥俩是当地出了名的铁匠,据说,他们打铁的手艺是祖传的。在闯关东时期,从“中国铁匠之乡”山东章丘来了一位谋生的铁匠--徐师傅,他挑着“挑儿”落户辽宁清原,成了当时清原一带最早的铁匠。多年后,徐师傅的儿子徐福禄来到新宾镇刘家村落脚,并将打铁的手艺传给了大儿子徐万祥、三儿子徐万海。
我们家这是祖传,现在光我知道的就是从我太爷和我爷爷,再到我父亲这辈,再就到我这辈。(记者:一共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呢?)按太爷这么算算到这一行也得一百七八十年。
刀耕火种的年代,打铁这项古老的行业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生存技艺,因此,打铁又被称为“现代工业的前身”。章丘铁匠天下闻名,曾经有“一盘红炉打天下”的美誉。徐师傅来到刘家村以后,铁匠铺的生意很红火。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徐家铁匠铺排队打铁的村民络绎不绝。
耳濡目染,徐万祥、徐万海哥俩很早就开始学习打铁,在他们的记忆中,父亲是慈爱的,同时也是严厉的。
我父亲还行,性格比较温顺,耐心,平时干什么活都告诉你怎么怎么干,因为是自己家,怎么都好说,不像生人,学徒,有那种关系,父子爷们在一起工作比较随便,教的时候也比较耐心,几乎就是手把手教给你,也打过。
父亲在打铁这一块教我们这些手艺挺严厉,名师出高徒,你要是师父不好你这个徒弟也是完蛋,干的也是不行。
“打铁还需自身硬,绣花要得手绵巧。”逼出来的手艺换来的是源源不断的生意,是乡亲们的认可。附近的村民都愿意到徐家铁匠铺打一些小农具,别看打的净是些牛马掌、斧子、镰刀等小物件,但是收入颇丰。同时,也不能小瞧了这些小玩意儿,打铁时只有稳、准、实,加上一些技巧,这些东西才能经得起使用。
打钉是一个人的活,自己就能干,打掌不行,必须得两个人,一个人干不了,这个活就是一个人干的活。(抡锤)主要是技巧的活,并不是说有多大劲才能够打了这个活,主要是技巧。
淬火必须得火赶得上,火赶不上你掐不来钉。赶火就是你拿过来什么色,几乎打完这钉还是什么色。淬火你蘸一下,回来一看,它有个蓝苗,蓝苗几乎退到头了,地上和点泥,插里头,严格来讲这就是正好。你要蘸镰刀时候就不能这么蘸,那个必须得蘸热火。
在铁匠铺里有这样一个规矩,就是所有打铁的工具都出自自家的铁匠铺,因此,徐万祥、徐万海哥俩所有的工具都是他们亲自打造的。而这个叫铁砧子的铁器是他们的宝贝,是父亲生前留给他们的。这样的铁砧子,哥俩一人一个,一个重200斤,另一个重150斤,每次用完后,兄弟俩都会将铁砧子运回家,第二天早上再运回来。
随着现代机械制造业的发展,机械化耕作取代了牛马等牲畜的田间劳作,代步工具也不再是畜力车,就连斧子、镰刀等常用农具也都闲置一旁,徐万祥、徐万海哥俩铁匠铺的生意开始冷清下来。
现在一年也就是两三万块钱吧,以前多的时候怎么也得十万左右吧。现在就不行了。以前几乎家家都有(牲畜)哇,现在,我们一个生产队只有一家养的,就一个牲畜。
看着堆放的牛马掌等这些小农器件,和炉膛里通红的火炭,曾经的门庭若市成为浮现在眼前虚幻的光影。当问及徐家铁匠铺会不会成为辽宁“最后一家”铁匠铺时,徐万祥、徐万海老哥俩的内心变得复杂起来。
从事这个行业的年轻人几乎已经是不干了,转向别的生存能力了,现在他也想干,但这种手艺他学的也少了,挣一年将能维持生活就不错了,所以说有的就改行了都。
怎么也得往下传,这是老祖宗的手艺,不传彻底就没有了,怎么也得想办法往下传,教会我的儿子,他们就是不干,手艺在自己身上,愿意什么时候干什么时候干,对吧,必须得往下传,不传肯定不行。
耳边叮叮当当的打铁声稀稀落落。作为一门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手工艺,它的渐渐衰退,只能成为人们心中一种追忆和无法避免的惋惜。面对这种“宿命”,徐万祥、徐万海老哥俩在做着最后的坚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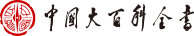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8139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8139号
